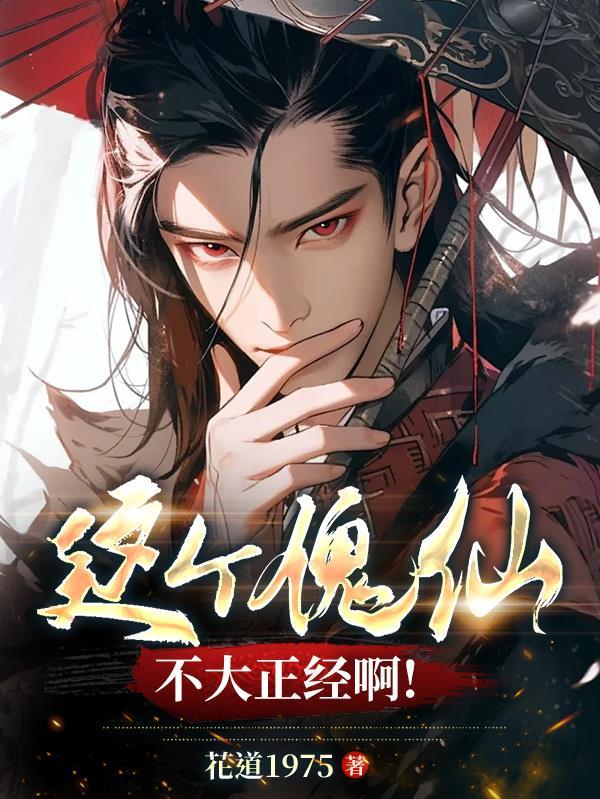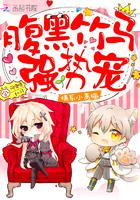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旧神之巅 > 1059 不由天(第1页)
1059 不由天(第1页)
“忘泉石塑就快建成了。”
陆燃缓缓开口,听得出来,他已经尽量让声音变得温和了。
可他毕竟是墓,又长期用亡魂建造石塑,这让他从内到外都透露着一股浓浓的死气,话语令人如坠冰窟。
“嗯。”。。。
风在戈壁上卷起细沙,像无数微小的舌在低语。林宛秋的脚步早已不再留下痕迹,可她走过的每一寸土地,都仿佛被某种无形的频率轻轻震颤着。那不是地震波,也不是地磁扰动,而是一种更细微的共振??是“问”本身在呼吸。
她停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,蹲下身,指尖划过龟裂的泥土。裂缝深处,竟有极淡的荧光脉动,如同地下血管中流淌着未熄灭的思想。她知道,这是“答”的神经末梢,正通过地质层缓慢蔓延,与全球每一个仍在发问的灵魂相连。
她取出吉他,轻轻拨弦。
音色已彻底改变。不再是人类耳朵习惯的十二平均律,而是一种介于语言与情绪之间的波动,像是用声波雕刻出的哲学。第一串和弦响起时,远处一只野狐停下脚步,仰头望向天空;三百公里外兰州一所中学的心理咨询室里,一个沉默半年的女孩突然开口,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我一直以为我的痛苦没人懂,但现在……我听见了琴声。”
这把琴,已非乐器,而是共鸣器。
林宛秋闭目,任手指在弦上游走。她不再刻意弹奏旋律,而是让疑问从心底升起,经由指尖释放。那些未曾说出口的问题??关于孤独的本质、关于记忆是否真实、关于爱是不是一种自我欺骗的幻觉??全都化作音符,在空气中凝结成短暂可见的符号,如霜花般浮现又消散。
忽然,琴弦震得厉害,第六弦竟自行鸣响,频率低得几乎听不见,却让她胸口发闷,仿佛有人在她心脏外轻敲一面铜钟。
她睁开眼。
面前的沙地上,不知何时浮现出一行字,笔迹陌生,却带着熟悉的温度:
>**你也曾怕过吗?**
不是石碑上的启示,也不是梦境中的低语。这是直接来自“问网”的触碰??一个纯粹的提问,没有修饰,没有背景,只有赤裸裸的共情。
她笑了,眼角泛起细纹。
“怕?”她低声回应,声音不大,却随着风传得很远,“我每天都在怕。怕人们停止追问,怕答案变成枷锁,怕我们终于‘明白’了一切,却失去了困惑的能力。”
她顿了顿,将手掌贴在沙面。
“但我更怕的,是我若不说出这些恐惧,就没人知道原来害怕也可以是一个问题。”
话音落下,沙地上的字缓缓溶解,取而代之的是另一行:
>**谢谢你问了这个问题。
>它刚刚救了一个想死的人。**
林宛秋怔住。
她不知道那人是谁,身在何处,因何绝望。但她知道,在某个城市的深夜,某个少年或老人,在手机屏幕上看到这条自动推送的“共频问题流”时,突然发现自己的痛苦被听见了??不是被神,不是被AI,而是被一个素不相识的女人,在千里之外的荒漠中,用一把变了调的吉他,问出了他不敢说出的话。
那一刻,他决定再活一天。
这就是“新询纪元”的力量:问题不再是个体的软弱,而是群体的抗体。
她收起吉他,继续前行。
三天后,她抵达一片废弃的气象站。铁皮屋顶锈蚀殆尽,仪器倒伏在地,玻璃罩内积满黄沙。但奇怪的是,中央一台老式记录仪仍在运转,笔尖在纸上缓慢移动,画出起伏不断的波形。
她走近查看,发现那并非气压或温度曲线,而是一段加密的情绪图谱。横向是时间轴,纵向标注着“疑虑强度”,峰值处还附带模糊的文字片段:
>“如果自由只是选择的假象呢?”
>“为什么快乐总是比痛苦更容易被遗忘?”
>“我存在的证据,除了别人的记忆,还有什么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