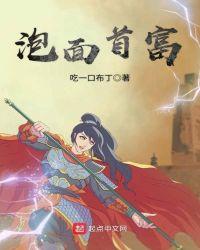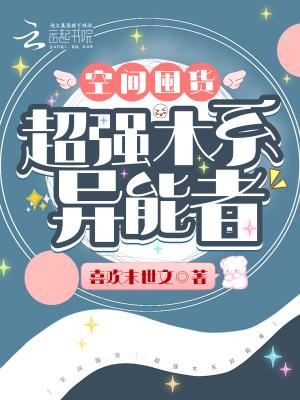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魅力点满,继承游戏资产 > 第七百一十八章 订婚宴(第3页)
第七百一十八章 订婚宴(第3页)
“见过几次。”她顿了顿,“她参加过一次家属开放日。那天她问我:‘你们做的这个东西,能让一个人忘记痛苦吗?’我当时回答:‘可以筛选记忆,但无法保证人格完整。’她听完,哭了。”
冯俊裕怔住。
母亲……问的是“忘记痛苦”?
他忽然想起,每年清明节,母亲都会独自去郊外一座无名墓碑前献花。他问是谁,她只说:“一个没能长大的孩子。”
难道……
他挂掉电话,翻出家中监控历史记录。昨晚他曾短暂回家取衣物,画面显示,母亲在他离开后走进书房,站了整整十五分钟,然后轻轻抚摸那本书的位置,低声说了句什么。
他放大音频,经过降噪处理,终于听清:
“你爸说过,真正的告别,不是死亡,而是被人彻底遗忘。”
冯俊裕浑身发冷。
他调出母亲过去十年的出行轨迹,发现每年七月十三日前后,她都会前往城西殡仪馆附属档案馆,停留约四十分钟。而七月十三日,正是父亲设定的密钥日期。
他连夜赶往档案馆。
通过人脸识别系统调阅当日录像,画面中,母亲手持一张特殊权限卡,进入B区地下二层??那里存放的是“医学研究遗体捐赠”名录。
她在编号Y-07的柜门前停下,输入密码,取出一份文件袋,翻开一页,指尖轻轻抚过某个名字,嘴唇微动,似在默念。
冯俊裕放大那个名字:
**K-01冯思悦女出生日期:2005。07。13死亡时间:2009。03。04捐赠单位:燕氏生命科学研究院**
冯……思悦?
他呼吸骤停。
这个名字,与他仅一字之差。出生日期,正是他生日的前一天。死亡时间,正是父亲笔记中提到K系列实验失败的时间。
难道……
他颤抖着手调出DNA比对程序,上传自己早年体检留存的基因样本,与K-01档案中的遗传标记进行交叉分析。
三分钟后,结果跳出:
>【匹配度:99。8%】
>【关系推断:同卵异胞胎】
轰??
仿佛一道惊雷劈开脑海。
他不是独生子。
他有一个妹妹,在五岁时作为“弦月计划”首批实验体死亡。而父母为了保护他,抹去了她的存在,连家庭相册中所有合影都被剪裁替换。
难怪父亲会选择“20150713”作为密钥??那是妹妹的第六个冥诞,也是他第一次在梦中见到她身影的日子。
难怪母亲每年都要去祭拜一个“陌生人”。
难怪她说“忘记痛苦”时会流泪。
因为他就是那个被留下的容器,承载着本该属于两个人的记忆与情感重量。
冯俊裕瘫坐在地,脑海中无数碎片终于拼合成完整的图景:
“初始共鸣者”之所以能成功,并非偶然。因为他的神经系统中,残留着妹妹未完成的情感回路。那是双胞胎之间天然存在的神经共振现象,被父亲加以利用,成为“原初引擎”唯一可行的生物载体。
而所谓的“第三份碎片”,根本不在他的大脑里,而在他对妹妹的潜意识记忆中??那份被压抑、被遗忘、却被身体永远铭记的血缘共鸣。
他终于明白,为什么清除协议需要两名“见证者”。
不只是因为基因标记。
而是因为,唯有当“失去的孩子”与“幸存的孩子”共同被记起时,系统才会承认??人性,仍未沦陷。
三天后,冯俊裕带着母亲来到郊外墓园。
雨又下了起来,细密如针。
他指着那座无名碑,轻声说:“妈,我知道她是谁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