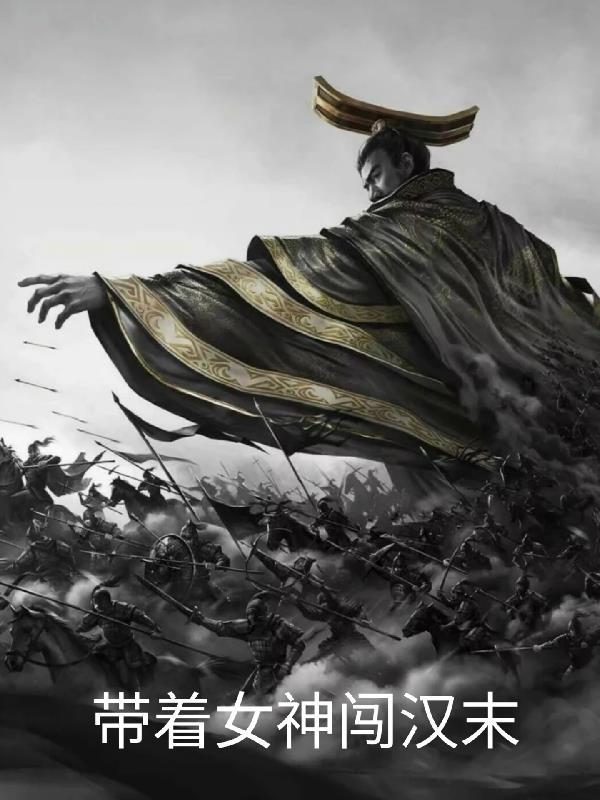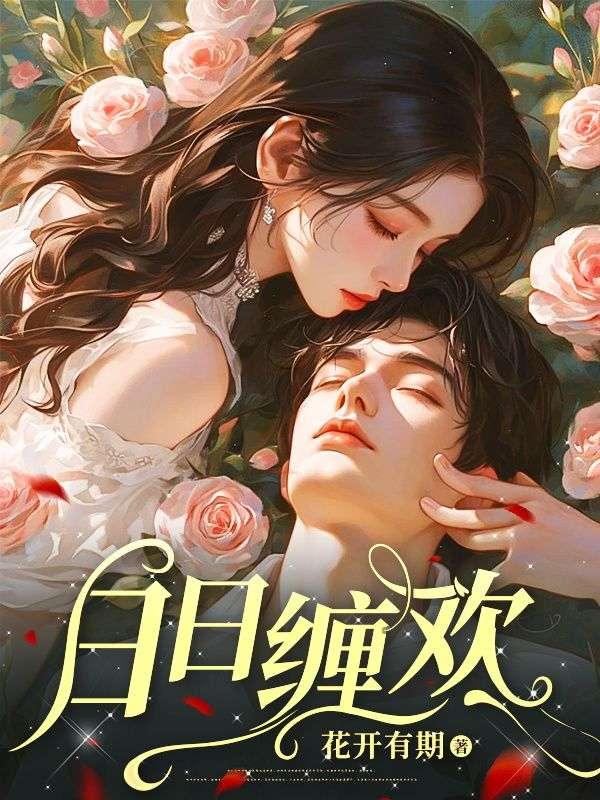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完蛋,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> 第911章玩吧谁能玩过你啊(第1页)
第911章玩吧谁能玩过你啊(第1页)
几大箱墨迹初干的答卷被整齐地码放在殿中央,如同沉默的山峦,压得人有些喘不过气。李治揉着发胀的眉心,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卷册,苦笑一声:“父亲这一手,真是给咱们找了个好差事。”
小武安静地在一旁整理。。。
夜色如墨,浸透荒庙的每一道裂缝。风从断墙间穿过,发出呜咽般的低鸣,像是无数未说完的话在游荡。那孩童端坐于残破蒲团之上,膝上摊开那本空白册子,纸页洁白得近乎刺眼,仿佛能吸走四周仅存的光。他不动,也不语,只是静静望着门外一片漆黑的野地,嘴角仍挂着那抹不合时宜的笑意。
远处传来犬吠,三声短,两声长。
他眼睛微微一亮,合上册子,轻轻放在身旁石台上。随即起身,赤足踩过碎瓦与尘土,走到庙角一口覆满蛛网的老井前。井口被一块青石半掩,上面刻着模糊符文,早已被风雨磨平。他伸手拨开石板一角,探出一根细竹竿,竿尾系着一只铜铃??铃身无舌,却在他指尖轻弹时发出一声极细微的“叮”,不似金属相击,倒像灵魂初醒时的第一声叹息。
“来了。”他说,声音依旧是少年的清亮。
不多时,林间沙沙作响,一个身影踉跄奔至庙门,扑通跪下。是个年轻女子,发髻散乱,脸上沾着泥灰,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布包,边缘渗出血迹。
“我……我带出来了。”她喘息着,将布包捧起,“《贞元实录》第三卷残本,藏在祖母棺中七十年,今日才敢取出。还有……还有十二位老人临终前口述的名单,全记在这帛上。”
孩童走过去,蹲下,不接,只盯着她的眼睛:“你不怕?”
“怕。”她咬牙,“可昨夜我梦见我爹了。他站在火里,一句话不说,就指着这本书。我知道,再不说,就真的没人记得了。”
孩童点点头,终于接过布包,动作轻柔得如同接过婴儿。他回到石台,掀开布包,取出一卷泛黄帛书,展开一角,墨字斑驳,但依稀可见“正月十七,童男六十入宫,皆称病愈”等句。他手指抚过文字,忽然闭眼,唇微动,似在默读。片刻后,整卷帛书竟自燃起来,火焰青白,无声无息,烧尽后灰烬并未落地,而是缓缓升空,如星屑般飘入那本空白册子的第一页。
纸面顿时浮现密密麻麻的字迹,标题赫然写着:
>**第十卷?第四章:火种不灭,在遗忘处重燃。**
女子惊愕地看着这一切,颤抖道:“这……这是《凤鸣》的新篇?”
“不是新篇。”孩童微笑,“是旧魂归来。”
他抬手,指向庙外北方天际。那里原本漆黑一片,此刻竟浮现出一抹极淡的红光,如同地底熔岩透过大地裂痕渗出。红光渐盛,映照出一座隐约轮廓??那是京城方向,太庙所在之地。
“祖灯开始动摇了。”他说,“当千万人开口,信仰便不再属于一人之手。他们以为用‘钦定版’就能封住真相,却不知真正的真言,从来不在朝廷印绶之中,而在母亲哄孩子入睡时哼的歌谣里,在老农数着年成时念叨的灾荒名目里,在寡妇扫墓时低声说的‘你走得冤’里。”
女子听得怔住,忽觉怀中一热。她低头一看,那原本空无一物的衣袋里,竟多出一支朱砂笔,笔杆刻着细小篆文:“言归其主”。
“这是……”
“守夜人的信物。”孩童说,“你已说出所知,便是新的执灯者。明日你回村,不必再藏这本书。告诉孩子们,读它、抄它、唱它。若有人来夺,你就把名字刻在树上;若有人来烧,你就把句子绣在衣角;若有人捂住你的嘴,你就用脚趾蘸血写在地上。”
女子含泪点头,正欲叩首,却被一股无形之力托起。
“去吧。”孩童轻声道,“记住,你说出口的每一个字,都在重塑世界。”
她转身离去,身影没入夜林。风起,吹散庙中余烬,唯余那本册子静静躺在石台,第一页的文字仍在缓缓延伸,如同根须深入土壤。
庙内重归寂静。
良久,井中忽然传出一声轻响,仿佛有东西从深处浮起。孩童走回井边,俯身凝视。黑暗中,一双眼睛缓缓睁开,不属于人类,也不属于鬼魅??那是文字本身的眼睛,由千万个被删改的句子凝聚而成,冰冷而清醒。
“你还记得吗?”井中传来回音,竟是陈知微的声音。
孩童笑了:“当然记得。你曾写下‘我不否认我是谁’,于是你成了不可抹除的存在。哪怕失语,哪怕沉睡,你的意志仍在书中呼吸。而我,只是帮你把故事讲下去的人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转柔:“其实,我一直想问你一件事??当初你写这本书时,有没有想过,它会把你吞进去?”
井中沉默片刻,再响起时,已是无数声音叠加:
有孩童背诵课文的清脆嗓音,
有老者讲述往事的沙哑低语,
有女子哭诉冤屈的哽咽,
有男子怒吼抗争的咆哮……
最终汇成一句:
>“我明知会被吞噬,才写下它。因为只有被真实吞没的人,才有资格唤醒真实。”
孩童仰头,望向屋顶破洞外的星空。银河横亘,宛如一本摊开的巨书,每一颗星都是一个未熄的名字。
他轻声道:“那么,接下来这一章,该由活着的人写了。”
与此同时,千里之外的南方村落,晨光初露。
那群孩子依旧围坐在槐树下,手中没有书,也没有纸。但他们口中齐声诵读着《凤鸣》,声音整齐如鼓点,穿透薄雾,惊起林鸟无数。他们的老师??那位曾冒雨讲书的少年??如今嗓子已哑,却仍坚持领读。每当他发声,喉间便渗出血丝,滴落在地,化作一朵朵青白小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