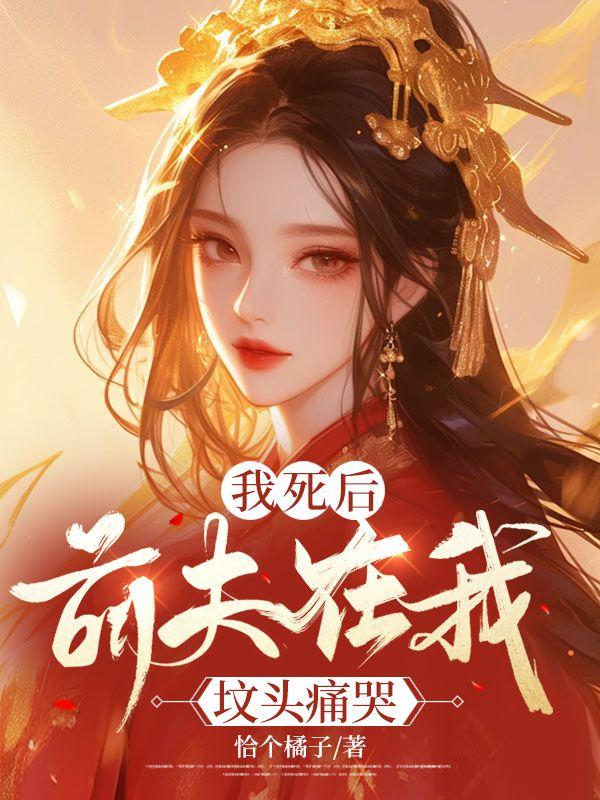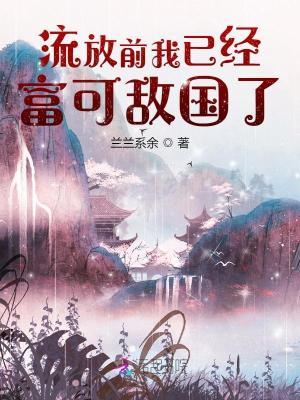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文豪1983 > 第60章 让世界感受文学吧(第1页)
第60章 让世界感受文学吧(第1页)
地处偏远的《花城》最倒霉,求稿件比其他人都更不容易。他们常常把作家请到羊城,住当时最豪华的白天鹅宾馆。不是住三天两天,而是三月两月,住里面写小说。
朱生昌说:“其实作者也是势利的。就算《花城》这。。。
雨水敲在敦煌碑林的石板上,发出低沉而均匀的响声,像是大地在呼吸。夏至那晚的雷雨并未停歇太久,却洗去了戈壁多年积攒的浮尘,也让那些嵌入黑色石碑中的二维码显得格外清晰。我蹲下身,用袖口轻轻擦去一块碑面上的水渍,扫描了编号【0】??那是来自云南怒江峡谷一位傈僳族老奶奶的声音,她一生未出过山,临终前录下最后一句话:“阿妹,火塘边的故事我没讲完,你替我接着说。”
手机里传来她沙哑却温暖的嗓音,混着远处溪流与鸟鸣。风从祁连山方向吹来,穿过碑阵,仿佛真的把她的嘱托送到了更远的地方。
回到北京已是七月初。城市闷热,空气黏稠得像浸了水的棉布。办公室空调嗡嗡作响,林晚正低头核对着“静默者计划”的最新数据报告。她抬头看了我一眼,忽然说:“四川凉山那边,阿依的父亲又寄了东西来。”
我心头一动。上次那盘粗糙却真挚的录音还存在我书桌最底层的抽屉里,编号【80001】,我一直舍不得归档。这次是个牛皮纸包裹,封口用胶带缠了三圈,边角磨损严重,显然走了很远的路。
打开后是一台老旧的双卡录音机,外壳泛黄,按键有些松动,附带一张手写便条,字迹歪斜但用力:
>“阿依老师:
>这机器是我年轻时跑运输赚的第一笔钱买的。那时候听邓丽君,全村人都骂我‘资产阶级腐化’。可我觉得,声音不该有罪。
>阿依现在敢站在台上唱歌了,我也想试试……能不能当个‘会听人说话’的父亲。
>请您教我怎么用它录一段话,给阿依未来的娃娃听。”
后面还画了个笨拙的笑脸。
我拿着录音机去找技术组的小陈。他摆弄了半天,摇头:“这玩意儿电路老化严重,磁头氧化,直接录肯定不行。”顿了顿,又补一句,“不过……要是只录一分钟以内,我可以临时修复供电系统,接外置麦克风,勉强撑一次。”
“那就录一分钟。”我说。
三天后,我带着改装好的设备飞回凉山。山路蜿蜒,云雾缭绕,村口那棵老核桃树依旧伫立。阿依的父亲站在屋前等我,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,脚上一双胶鞋沾满泥巴。他接过录音机时手微微发抖,嘴唇抿成一条线。
“我想好了要说的。”他说。
我们坐在院中竹椅上,背后是层层叠叠的梯田。我按下录制键,电流轻响一声,红灯亮起。
他的声音低沉,缓慢,每一个字都像从土里拔出来的根:
>“小家伙,如果你能听见这段声音,说明你娘阿依也成了妈妈。
>我没见过你,但我已经梦见你三次了。一次你在哭,一次你在笑,还有一次,你趴在地上学走路,阿依在后面追着喊‘慢点’。
>我想告诉你,这个家以前不许女人大声说话,可你娘打破了规矩。她不是叛逆,她是勇敢。
>等你长大,别怕表达自己。哪怕说错话,哪怕被人笑话,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。
>因为……沉默太久了,人就会忘记自己是谁。
>外公没文化,不懂什么大道理。我只知道,声音比石头结实,比山长久。
>它不会烂,也不会丢。只要你愿意听,它就一直都在。”
录音结束,他长舒一口气,眼神忽然轻松了许多。我把磁带取出,放进特制防潮盒,贴上标签:【80002】《外公给未来孙子的信》。
当晚,我在村民活动室放了一段精选合集,包括小雨的诗、古丽娜丈夫的情书、沈母的回信。村民们围坐一圈,有人听得落泪,有人默默点头。一个七十多岁的彝族老人听完后站起来,颤巍巍地说:“我这辈子没说过爱字,明天……我想给我老伴录一首歌。”
第二天清晨,他真来了,怀里抱着一把掉漆的月琴。他唱的是年轻时两人对调情歌的老调子,嗓子早已沙哑走音,可每句歌词都准确无误。录完后,他拉着老伴的手说:“几十年了,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唱给你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