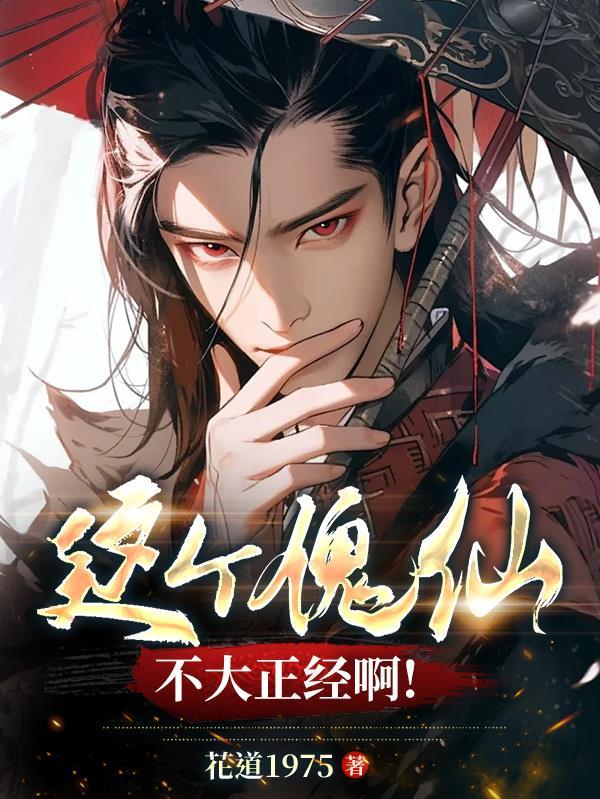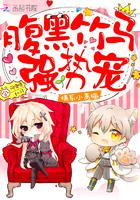书迷阁>1987我的年代 > 第695章 这就是幸福(第2页)
第695章 这就是幸福(第2页)
饭桌上,村医老杨说起昨夜灾情:“两个娃都是骨折,一个左腿,一个右臂。卫生所没X光机,也没止痛药,只能用夹板固定。家长守了一夜,哭得嗓子都哑了。”
林小满放下碗筷:“马上架设‘萤火盒子’,我要连线华西骨科专家。”
十分钟后,屏幕亮起。高清镜头下,孩子的伤处清晰呈现。专家一边指导复位手法,一边叮嘱用药剂量。林小满亲自操作,阿杰协助固定,小周记录医嘱。当最后一个绷带缠好,已是凌晨两点。
第二天清晨,全村聚集在晒谷场。林小满站在一块青石上,面对一百多人的目光,声音坚定:“我们知道你们苦。路不通,电不稳,孩子上学要爬绳梯。但我们来了,就不会空手回去。”
她宣布三项计划:一是建立远程诊疗站,每周两次专家会诊;二是启动“云端课堂”,为辍学儿童提供义务教育课程;三是培训本地青年成为“萤火联络员”,负责设备维护与信息传递。
“我不是来施舍的。”她说,“我是来交钥匙的。这扇门一旦打开,就永不关闭。”
人群中,一位年轻女子举起手:“我能报名当联络员吗?我高中毕业,在外打工五年,今年回来照顾生病的母亲。”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林小满问。
“赵春梅。”
“欢迎你。”她微笑,“明天就开始培训。”
仪式结束后,林小满独自走向村后的?望台。那里有一棵老核桃树,枝干扭曲如龙。树下坐着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,正低头画画。
“你在画什么?”林小满轻声问。
女孩抬起头,眼睛清澈见底:“我在画桥。”
“桥?”
“嗯。电视里那种,很大很大的桥,有灯,有车,能把我们接到城里去。”她指着画纸,“我还画了学校,白色的楼,操场上有国旗。”
林小满鼻子一酸。她蹲下身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“阿朵。”
“阿朵,你知道吗?你画的这座桥,已经在图纸上了。三年后,它会真的出现在这里。”
小女孩眨眨眼:“真的?”
“真的。而且,你会是第一个走过它的人。”
那天下午,林小满组织村民召开“萤火议事会”。议题只有一个:如何用有限资源优先解决最紧迫问题。
争论激烈。有人主张先修路,有人坚持先通电,还有人提出应该先把孩子送到山外读书。
最后,一位白发老人站起来,他是村里最年长的长者,名叫石阿公。
“我活了八十二岁,见过太多人走了又回来,哭了又哭。”他声音沙哑,“但我没见过谁像你们这样,不问我们要钱,反而给我们本事。所以我说一句??先让孩子读书。路可以慢慢修,电也可以等等,可孩子的年纪,一天都等不得。”
全场寂静,继而爆发出掌声。
当晚,第一堂“云端课”开讲。教室是腾出来的村委会活动室,投影仪连上卫星网络,屏幕上出现成都实验小学的语文老师。
“同学们好,我是李老师。”温柔的声音响起。
孩子们齐声回应:“李老师好!”
阿朵坐在第一排,笔记本写得工工整整。她旁边是个小男孩,缺了颗门牙,却笑得灿烂。
林小满站在门口,看着这一幕,眼眶发热。她掏出红色笔记本,写下:
>**第1126天**
>今天,我听见了朗读声。
>不是广播里的,不是录音机里的,
>是六十个孩子齐声念《静夜思》的声音。
>床前明月光,疑是地上霜。
>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