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迷阁>红楼之黛玉长嫂 > 196第 196 章(第1页)
196第 196 章(第1页)
风雪再起时,已是次年春寒料峭。长安城外的官道上,一队青衣女子踏雪而行,每人肩扛竹简、背负笔墨,自各地女子书院而来,汇聚于明慧书院门前。她们手中捧着的,是三年来各地女子工坊账册、婚嫁纠纷案卷、地方女巡司判例汇编??皆为《女子权益法典》初稿所需之实证。
黛玉立于门首,白发在风中微扬。她已不再穿紫金官袍,只着素色布裙,腰间系一条旧丝绦,那是母亲生前留下的遗物。沈素衣上前禀报:“先生,三百六十七州县资料俱已送达,共得案例九千八百二十三宗,其中逼嫁夺产者占六成,虐婢焚书者两成,其余皆为继承权争讼。”
“很好。”黛玉轻声道,“把所有涉及人命的案子挑出来,先列条文。”
众人入堂议事。烛火通明,纸页翻飞。柳青鸾指着一份江南呈报的卷宗,声音发颤:“苏州府周氏族长以‘败坏门风’为由,将亲侄女活埋于祖坟侧室,只因她不愿守寡,欲改嫁商贾。那女子临死前咬破手指,在棺木内壁写下‘我愿为人,不作贞鬼’八字……”
满堂寂然。
霍七娘猛然起身,剑柄撞桌有声:“此等禽兽,岂能容其逍遥法外?当诛九族!”
黛玉却缓缓摇头:“杀一人易,改一俗难。若我们只以暴制暴,便与那些压迫者无异。我们要做的,不是复仇,而是让天下再无此类悲剧发生。”
她提笔蘸墨,在宣纸上写下第一条:“凡女子年满十六,即具完全民事之权,父母宗族不得强拘其身、擅定其婚、夺其财产。”
第二条:“婚姻自主,两情相悦为本。强迫成婚者,以非法拘禁论;致人死亡者,按谋杀罪惩处,主犯斩首,从犯流徙三千里。”
第三条:“女子享有同等继承权。嫡庶不分,长幼同列。若有隐匿遗嘱、篡改分单者,除追回全部资产外,另罚其家产半数充作女子助学基金。”
字字如刀,句句如铁。
夜深人静,众弟子散去,唯紫绡仍守在旁。她见黛玉伏案太久,便劝道:“姑娘歇息吧,明日再续。”
黛玉抬眼望向窗外,雪光映着烛影,恍若星河倒悬。她忽然问:“紫绡,你还记得小时候被卖进林府的事吗?”
紫绡一怔,低声道:“怎会不记得?那日天也这般冷,我娘抱着我哭,说‘只要活着,总有出头之日’。后来您救了我,教我读书写字,让我明白,奴婢也可以抬头做人。”
“所以这部法典,不只是为了千年后的人看。”黛玉轻抚案上草稿,“是为了告诉每一个正在受苦的女孩:有人记得你,有人为你痛,有人愿意用一生去改变这世道。”
话音未落,门外忽传急步声。一名女巡司快骑冒雪而来,跪地呈上一封加急文书:“启禀先生!河北道传来噩耗??三名参与编修法典的基层女吏,在归乡途中遭蒙面人袭击,两人重伤,一人殉职。凶手在现场留下血书:‘妇人议政,天理不容’!”
堂内灯火猛地一晃。
沈素衣怒极反笑:“他们怕了……他们终于怕了!”
柳青鸾拍案而起:“请下令彻查!我率女卫亲赴河北,掘地三尺也要揪出幕后黑手!”
黛玉闭目良久,终是睁开双眼,眸光清冽如冰泉:“不必追查。”
众人愕然。
她站起身,缓步走到墙边,取下悬挂多年的金凤北斗令旗,轻轻拂去尘埃:“你们可知,为何我不让乌兰挥师南下?因为我深知,真正的敌人,不在边关,也不在朝堂,而在人心深处那一片根深蒂固的黑暗。他们不怕刀兵,不怕律令,只怕女子真的站起来。”
她转身面对众人,声音不高,却字字千钧:“从今日起,《女子权益法典》编修之地,移至皇城太庙东阁。皇帝已下旨,此地由女政司专掌,禁军护卫,昼夜巡防。凡参与编修者,皆授七品待诏衔,享朝廷俸禄,家属纳入官府庇护。”
“至于那三位女吏……”她顿了顿,眼中泛起泪光,“厚葬于女子先贤祠侧,赐谥‘贞毅’。殉职者之妹,即日起入学传习所,免一切杂役,由我亲自教导。”
命令下达后第三日,法典编修正式迁入太庙。那日清晨,三百余名女学士列队而行,手持竹简,身披红绶,自明慧书院出发,一路吟诵新编《女训歌》:
>“不拜牌坊拜学堂,
>不焚脂粉燃心香。
>笔墨为剑斩枷锁,
>法典成书照四方。”
百姓夹道相迎,妇孺跪地叩首,老妪含泪高呼:“我家孙女也能上学了!”
就在众人行至朱雀大街时,忽有一群儒生冲出人群,手持腐烂菜叶与臭鸡蛋,狂喊“牝鸡司晨,祸乱纲常”,欲投掷队伍。
尚未靠近,霍七娘一声令下,二十名女卫疾步而出,手持短棍,列阵拦截。场面一度混乱。
此时,走在最前的黛玉却忽然抬手制止。她缓步上前,直面那群儒生,目光平静:“你们骂我妖妇,说我乱伦常。可你们可曾去过女子工坊?可曾见过被逼殉节的母亲?可曾听过深夜里多少女孩哭着说‘我不想死’?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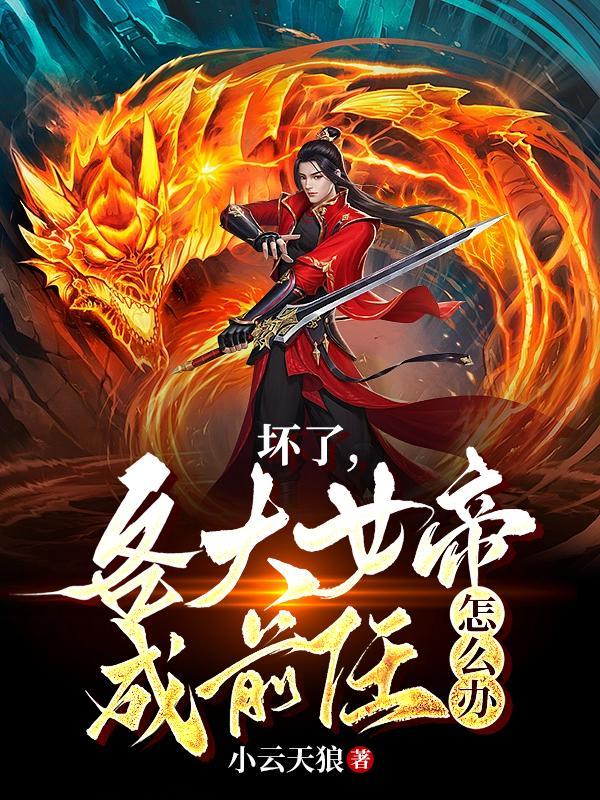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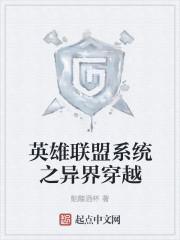
![七日逃生游戏[无限]](/img/31396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