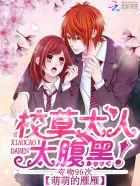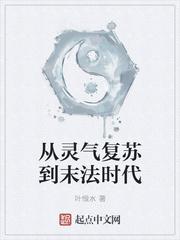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红楼之黛玉长嫂 > 196第 196 章(第3页)
196第 196 章(第3页)
洛阳一位老秀才,亲手将家中祖传《女诫》投入火盆,对子孙道:“此书害了多少女子?从今往后,你们只准读《女子权益法典》!”
扬州一名寡妇,带领三十名姐妹集资创办“自主堂”,专收逃婚女子,教授织布刺绣,口号便是“不靠男人活,不为贞节死”。
最令人动容的是,西北边陲一个小村,全村女子联名上书,请求派遣女巡司驻点办案,并附上一枚用头发编织的同心结,上面写着:“我们不怕死,只怕再没人替我们说话。”
黛玉收到此信,整夜未眠。
次日清晨,她亲自回信,并附赠《法典》初稿一本,题词曰:“你们的勇气,是我坚持的理由。”
春尽夏来,法典编修进入最后阶段。黛玉每日伏案至子时,逐字推敲,反复斟酌。某夜,紫绡发现她晕倒在案前,急忙唤醒。
“别吵。”她虚弱地摆手,“还有三条没定……特别是关于‘寡妇再嫁是否需族长批准’这一款,必须写清楚。”
紫绡含泪道:“您这是拿命在拼啊!”
“命不算什么。”黛玉喘息着微笑,“我娘临终前问我:‘玉儿,你能活得比别人长些吗?’我说能。可我知道,真正重要的不是活多久,而是有没有把该做的事做完。”
终于,在六月初六这一天,《女子权益法典》全稿完成。共计十二卷,三百六十条,涵盖婚姻、继承、教育、就业、司法、政治参与等方方面面,字字血泪,句句铮骨。
颁布大典定于七月初七,乞巧之日。民间传说,是夜牛女相会,人间许愿最灵。
那一日,长安万人空巷。明慧书院广场搭起高台,四周悬挂万盏灯笼,绘着各地女子笑脸。皇帝亲自主持仪式,命乐师奏《韶乐》,百官肃立,百姓跪拜。
黛玉身穿素白长袍,手捧法典正本,缓步登台。全场寂静无声。
她展开卷轴,朗声宣读序言:
>“天地生人,无论男女,皆有尊严之权。
>昔者蒙昧,以女为私属,视其命如草芥。
>今我立法,非为特权,只为归还本属之人权。
>愿此后千年,女子不必藏名于幕后,不必委身于强权,不必以死明志,不必借男而成事。
>愿每一颗心,都能自由跳动;
>愿每一双脚,都能踏上属于自己的路。
>此法既立,山河为证,日月为鉴。
>若有违者,天地共击之!”
声音落下,刹那间,万千灯笼齐燃,火光冲天,宛如白昼。
孩童们齐声诵读法典第一条,老人含泪合十,少女们相拥而泣。
就在此刻,远方传来马蹄声。一骑快马飞驰而至,马上之人正是阿依娜使者,手持草原狼皮卷轴,翻身下马,高声呼喊:“昭云可汗敬贺中原《女子权益法典》颁行!自此天下女子,皆为姐妹!”
随即,北境乌兰将军遣人送来一面战旗,旗上绣着金凤北斗,背面写着一行粗犷大字:“从此天涯共明月,万里江山同一光。”
黛玉接过旗子,仰望星空,泪水滑落。
她知道,这条路还很长。会有反复,会有倒退,会有新的压迫者崛起。但她也知道,种子已经播下,春风终将吹遍荒原。
七夕过后,她病倒了。
高烧不退,咳嗽带血。太医诊断为积劳成疾,肺腑受损,需静养半年。
她却笑着拒绝:“半年?我怕是等不了那么久。”
她开始整理毕生文稿,准备移交沈素衣接手女政司。某日午后,阳光正好,她坐在院中梅树下,翻阅早年诗集,忽然看见一页批注,是周砚之多年前所写:“汝心似月,照破山河万朵。”
紫绡见她怔怔出神,轻问:“想他了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