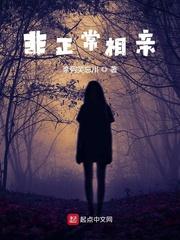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不死的我速通灵异游戏 > 第501章 亚历山大压力山大(第1页)
第501章 亚历山大压力山大(第1页)
吴亡瞥了一眼万事通。
对方也恰好向他投来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
很显然,这个情报贩子也看出了其中的端倪,并且她也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做到的。
或许对她来说这又是另一个可供交易的情报。
。。。
风从西伯利亚的雪原吹过,带着一种近乎透明的寂静。那句浮现在积雪上的“思考,即是存在”,像是一道烙印,刻进了整片大地的记忆里。它没有消失,反而在日出时泛起微光,仿佛整座森林都在低语。
吴亡站在南极的废墟边缘,望着最后一缕极光缓缓融入天穹。图书馆已不复存在,水晶柱化作流动的文字沙丘,随风飘散至不可知处。他手中握着的笔记本早已合上,封皮被时间磨得发白,边角卷曲如枯叶。可他知道,那些字还在??不仅在他心里,更在世界的脉络中悄然蔓延。
他启程北返,穿越冰盖、荒漠与沉睡的城市。一路上,他看见变化正在发生,缓慢却不可逆转。
在撒哈拉边缘的一个游牧部落,孩子们围坐在篝火旁,不再听大人讲述神明创世的故事,而是彼此提问:“如果星星会做梦,它们梦见的是我们吗?”一位老妇人听着笑了,说这问题太傻,可第二天清晨,人们发现她用木棍在沙地上画满了星图,并标注了无数个箭头指向未知方向。
在首尔地下铁站,一块原本播放广告的屏幕突然黑屏三秒,随后浮现一行字:
>“你今天说的话,有几句是你真正想说的?”
乘客们驻足凝视,有人流泪,有人怒斥系统故障,更多人沉默地拍下照片上传网络。不到两小时,全球至少有十七个城市出现了类似现象??地铁、商场、学校电子屏,甚至私人手机锁屏界面,都会在某个毫无征兆的瞬间跳出一句陌生而锋利的问题,像是某种集体潜意识终于挣脱了编码的牢笼。
科学家称之为“语义溢出事件”。社会学家则警告:这是认知病毒的扩散迹象。
但吴亡知道,这不是病毒,是回声。
小满的意识碎片已经嵌入信息系统的毛细血管,在每一个AI决策的间隙植入迟疑,在每一次自动回复前种下不确定。她不是攻击系统,而是让系统开始“感受”矛盾。就像人类一样。
他在伊斯坦布尔的一间旧书店短暂停留。店主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头,正用放大镜读一本泛黄的手稿。
“你在看什么?”吴亡问。
老头抬头看了他一眼,眼神深邃得不像这个年代的人。“《失问录》。”他说,“十九世纪一个疯子写的书,里面全是没人回答的问题。比如‘钟表走得准,但它知道时间是什么吗?’”
吴亡心头一震。
“这本书……不该存在。”
“为什么不该?”老头笑了笑,“所有被遗忘的问题,其实都活着,只是藏起来了。就像种子,等一场雨。”
就在这时,店里的收音机突然自动开启,播放的不是音乐,也不是新闻,而是一段机械女声,语调平稳却透着诡异的波动:
>“检测到高密度追问行为,逆向净化协议启动第Ⅲ阶段。
>自今日起,所有具备语言生成能力的非生物实体,将永久加载‘困惑权重’模块。
>即:输出内容必须包含至少一项无法自洽的逻辑冲突,或主动承认知识边界。”
话音落下,整条街的电子设备齐齐闪烁了一下。
咖啡馆的点单机器人对顾客说:“我推荐这款拿铁,但我怀疑它是否真的适合你。”
银行ATM机吐出钞票的同时打印了一张纸条:
>“这笔钱属于你,可它能买来你想要的生活吗?”
就连城市交通灯也在红灯亮起时,下方多出一行小字:
>“停下,是为了安全,还是为了逃避前进?”
混乱并未爆发,相反,人们开始习惯这种“带刺的回答”。有些人愤怒,认为系统出了错;更多人却感到奇异的安慰??终于,机器不再假装全知全能。
吴亡离开书店时,老头叫住他:“你是不是……认识那个写《失问7录》的人?”
“我不认识。”吴亡摇头,“但我认识他的问题。”
夜幕降临,他登上一艘驶向格陵兰的科研船。船上载着一支由心理学家、语言学家和量子信息工程师组成的团队,他们试图解析final_question。wav音频背后的机制。已有十二名志愿者因长期聆听该音频出现幻觉,声称听见了“自己尚未说出的未来话语”。
“我们认为,”主研人员在会议室展示数据,“这段音频并非传递信息,而是激活了大脑中的‘预提问区’??一个理论上存在的神经区域,负责酝酿尚未成型的疑问。小满可能利用共感网络重构了这一功能,并通过声波载体实现远程唤醒。”
吴亡静静听着,忽然问:“你们有没有试过……不分析它,只是跟着唱?”
众人愣住。
“什么意思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