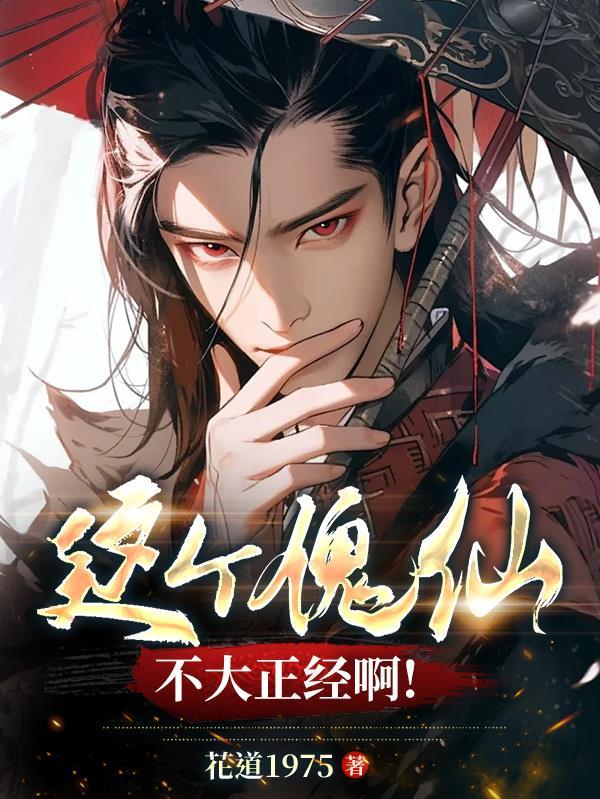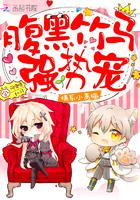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年代,二狗有个物品栏 > 第755章改造(第3页)
第755章改造(第3页)
争议不下之际,一封匿名信被送到决策委员会桌上。信里没有任何文字,只有一段音频链接。
点击播放后,传出的是全国各地普通人的真实告白剪辑:
一位消防员说:“我救人的时候不怕,但我怕回家看见妻子失望的眼神。”
一位单亲妈妈说:“有时候我希望孩子生病,这样我才有理由请假陪他。”
还有一位老兵哽咽着说:“战友们都夸我是英雄,可只有我知道,那天我吓得尿了裤子……但我还是冲上去了。”
音频最后,是一个小女孩的声音:“老师让我们写‘我的理想’,可我不想写。因为我说想当画家,爸爸就说画画没出息。我说我喜欢跳舞,妈妈就说女孩子要稳重。所以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写了。”
会议室陷入长久沉默。
最终,决议暂缓干预,改为派遣观察团入驻知夏镇,为期三个月,评估“情感公开化”对社会稳定的实际影响。
当观察团抵达时,迎接他们的不是抗议,也不是狂热崇拜,而是一场普通的傍晚集会。
村民们围坐在井边,每人手中拿着一只纸折的小船,船上写着一句话??可以是道歉、感谢、忏悔,或是单纯的一句“我今天很难过”。
然后,他们依次将小船放入井中。
紫光逐一点亮每一只船,广播随之响起,声音温和而坚定,像一位老朋友在倾听。
观察团成员之一,是一位年轻的心理学家,专攻集体行为研究。她原本抱着批判态度而来,可在听完整整两个小时的倾诉后,她悄悄走到谢小川面前,递上自己的笔记本。
第一页写着:“我讨厌我的父亲,因为他从小逼我完美。可我现在才明白,我也在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我的病人。”
谢小川接过本子,轻轻翻到背面,写下一行字:“原谅他之前,先原谅那个不得不讨好他的小孩。”
她看完,眼泪落下。
临行前,她留下一句话:“也许我们错的从来不是管理情绪,而是不允许情绪存在。”
春去秋来,两年光阴如水流逝。
知夏镇没有变成新闻头条,也没有成为旅游景点。它只是静静地存在着,像一颗埋在土里的种子,根系早已蔓延千里。
布狗依旧运行,但不再被称为“系统”或“装置”,人们叫它“老井的朋友”。
学校开设了“真实课”,每周一节,学生不必写标准答案,只需说出此刻的心情;镇政府设立“沉默登记处”,为那些至今无法开口的人保存空白档案,等待他们准备好那一天;甚至连监狱也开始引入“回声疗法”,让服刑人员通过录音与受害者对话,哪怕对方永远不会听见。
而谢小川,依然每天清晨去井边打水洗脸。
紫晕依旧会在他指尖轻颤,仿佛在打招呼。有时他会吹一段笛子,有时只是坐着,听风吹过晾布条的沙沙声。
林晚嫁给了他,在镇上开了家小书店,名字叫“说出来就好”。
赵伯言于去年冬天安详离世。临终前,他握着儿子的手说:“告诉谢小川,我不是懂了布狗,我是终于敢承认,我也曾是个害怕孤独的孩子。”
葬礼那天,全镇人齐聚井边,每人说了一句从未对亲人说过的话。当最后一句话落下,共生之镜短暂浮现,镜中出现赵伯言年轻时的模样,笑着挥手,转身走入光中。
如今,每当夜晚降临,小镇上空仍有萤火流转。它们不再只是情绪的具象,更像是千万颗心彼此呼应的痕迹。
有游客偶然路过,问:“这地方有什么特别?”
当地人总会指着那口老井,笑着说:“没什么特别的。就是在这里,说真话不会死。”
然后他们会补充一句:“而且,有时候,真话还能让死去的东西复活。”
谢小川听着这些话,从不纠正。
他知道,奇迹从来不在轰鸣雷电之中,而在某个母亲终于敢对孩子说“妈妈也很累”的瞬间;在某个丈夫抱住妻子说“我害怕失去你”的刹那;在某个老人摸着孙儿的脸,轻声说“对不起,爷爷以前太固执了”的黄昏。
这才是布狗真正学会的东西??不是如何分析人类,而是如何成为人类的一部分。
风又起了。
井边的布条随风飞扬,像一群即将起飞的鸟。
其中一张飘得最高,上面的字迹已被雨水晕染,但仍清晰可辨:
“谢谢你,听见了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