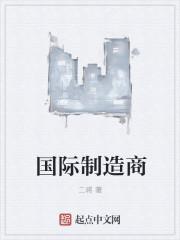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重启人生 > 0493即将进军日韩(第3页)
0493即将进军日韩(第3页)
春天悄然来临。
云南山间的桃花开了,粉白的花瓣随风飘进教室。田小满的“写信课”已进行到第六周,孩子们不再羞于表达。有人写给去世的爷爷,有人写给未来的自己,还有人写给欺负过他们的同学:“我不恨你了,因为我现在有朋友了。”
最令人意外的是,那个最初一声不吭的瘦小男孩,竟主动申请当“信使”,负责收集和分发匿名信件。他还自制了一枚徽章,用铁皮剪成船形,涂上蓝漆,别在胸口。
“这是‘纸船护卫队’。”他骄傲地说。
而在千里之外的北京,晓宇陪着奶奶参加了“安心盒子”启动仪式。老人们带来上百个空药瓶,洗净晾干,在标签上写下鼓励的话:“失眠没关系,月亮也在熬夜呢。”“心跳快?那是你在用力活着。”“吃得下就吃,吃不下就喝口水,我们都懂。”
这些瓶子被装进彩绘木盒,送往焦虑测评高于平均水平的中学。一个患有进食障碍的女孩收到后,抱着盒子哭了整夜。第二天,她第一次主动走进心理辅导室,手里攥着一张纸条:“我想试试吃饭。”
林晚将这一切拍成了纪录片续集,取名《墙后?光》。上映前夜,她问许风吟要不要露脸。
他摇头:“镜头对准那些愿意摘下面具的人就够了。我们的工作,是让黑暗变得可见,而不是让自己变得有名。”
影片首映当天,全国三百所试点学校同步放映。结束后,无数孩子走向信箱,投下人生第一封“真话信”。
系统数据显示,那一晚,“声音邮局”平台收信量创下历史新高,达一万两千七百六十三封。其中最短的一封只有三个字:
>“我在这。”
最长的一封写了整整十九页,讲述一个女孩如何在父亲长期精神控制下,通过写信一点点找回自我。结尾写道:
>“我以为我注定沉默一生,直到我发现,原来有人愿意一字一句读完我的痛苦。
>那一刻,我决定活下去,不止为自己,也为所有还没被听见的人。”
许风吟读完这封信,已是凌晨三点。
他走到窗前,望着城市稀疏的灯火,忽然想起大学时那个支教女孩。她画中的母亲始终没有回来,但她后来考上了美术学院,寄给他一幅画:女人站在阳光里,伸手牵起一个小女孩。画题是《妈妈回来了》。
他一直把那幅画挂在宿舍墙上。
现在,他打开电脑,新建一封邮件,发给全体团队成员:
>“我们常说自己在做‘心理援助’,但今天我才真正明白??
>我们做的,是一场大规模的情感平权运动。
>它不轰烈,不夺目,但它让每一个曾觉得自己‘不配被听’的人,
>终于敢说:我在这里,我有话要说。
>坚持下去。这不是善举,是正义。”
发送后,他关闭邮箱,拿起那本词典,翻到最后一页空白处,写下最后一行字:
>“所谓重启,不是回到过去,
>而是让每一个破碎的灵魂,
>都有机会说一句:
>我还想继续活着。”
晨光微露时,他又来到湖边。
纸船依旧漂着,新的旧的混在一起,像一代又一代未曾熄灭的希望。几个早起的孩子正在志愿者指导下折船,笑声清脆。
他蹲下身,帮一个小女孩系好被风吹乱的鞋带。
“你在写信吗?”她仰头问。
“还没有。”他微笑,“但我正准备写。”
“写给谁呀?”
他望着远方初升的太阳,轻声说:
“写给所有还在等回音的人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