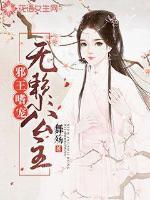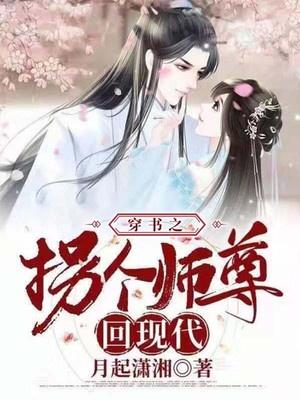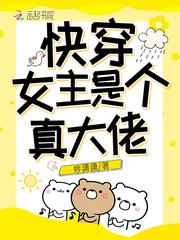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霍格沃茨:这个黑魔王正得发邪 > 第574章 第四天灾(第2页)
第574章 第四天灾(第2页)
>每一位学生都将拥有两名导师:一名教授技能,另一名倾听故事。
>所有课程始于一个问题:你今天为什么哭泣(或为何欢笑)?
>考试从不测验答案,只记录真诚。”
第二天清晨,三百七十二名新生陆续抵达北海道边境。他们来自战火纷飞的难民营、被遗忘的孤岛村落、高压统治下的封闭城市……每个人身上都带着不同的伤痕。
一个戴眼罩的非洲少年递上报名表,上面写着:“我想学会不用拳头表达愤怒。”
一位年过六旬的老妇人颤巍巍提交申请:“我孙子死于校园枪击案。我想知道,恨能不能变成守护的力量?”
还有一位匿名寄来的信件,附着一小撮灰烬:“这是我烧毁家族仇恨日记时留下的。我愿意重新开始。”
最引人注目的,是那个从新伊甸遗址走出来的“未命名”孩子。他始终低着头,身穿宽大病号服,手腕上有电极灼伤的痕迹。登记员问他姓名时,他久久不语,最后抬起手,在纸上画了一朵歪斜的樱花。
“那就叫你‘樱’吧。”卢娜接过笔,在备注栏添了一句:“擅长沉默中的呐喊。”
招生结束当晚,艾登召集核心团队召开首次校务会议。地点设在尚未完工的教学楼地基中央,头顶星空璀璨。
“师资问题必须解决。”伊莱娜翻开资料,“我们需要精通共感能力引导的心理学家、神经语言学家、跨文化沟通专家……目前全球符合条件的人不足五十。”
“我们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老师。”艾登说,“我们需要的是‘见证者’。”
他闭上眼,启动共感广播。
>“致所有曾被世界否定过情感的人:
>你是否曾在深夜痛哭却不被理解?
>你是否因太过敏感被视为弱点?
>你是否在群体中感到孤立,因为你感知到了别人忽略的悲伤?
>如果你回答‘是’,那么你正是我们要找的人。
>来吧。在这里,你的伤口将成为灯塔。”
讯息发出后的第七十二小时,回应如雪崩般涌来。
一位自闭症艺术家发来视频:他能看见情绪的颜色,多年来被人当作怪胎,如今愿教学生“如何用画笔翻译心灵”。
一名前战地记者写道:“我在爆炸现场听见亡者最后的思念。我不怕死亡的声音,只怕活着的人装作听不见。”
甚至还有一位年迈的清洁工阿姨留言:“我没读过书,但我每天打扫医院走廊时,都能感觉到哪些病房藏着无声的告别。我想学着说一句‘我懂’。”
艾登一一回复,邀请他们加入。
与此同时,维克托悄然离开了疗养院。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只留下一封信给艾登:
>“你说得对。我想让她活下去的方式错了。
>真正的纪念,不是复制她的意识,而是延续她的选择。
>她最后画的那幅画,其实有第三个人??站在远处微笑的女人,标签写着‘陌生人阿姨’。
>她记得那个在地铁口帮她捡起散落画纸的路人。
>所以我要去找她。告诉她,有个女孩,直到最后一刻,依然相信善意。
>这就够了。”
风吹散纸页,艾登望着远方山脉轮廓,忽然问道:“你说,共感能力究竟是天赋,还是诅咒?”
卢娜靠在他肩上:“都不是。它是责任??听见之后,要不要回应的责任。”
几天后,施工队完成了教学楼主体框架。当最后一根梁柱落定时,整座建筑突然轻微震动。埋藏在地基中的晶石阵列自发激活,释放出柔和蓝光,顺着纹路蔓延成树状图腾,竟与樱林根系产生共鸣。
一夜之间,原本只打地基的地方,长出了十二棵半透明的水晶树,每棵树冠都悬浮着一个人格象征物:火焰、书本、盾牌、音符、显微镜、面具、羽毛笔、钟摆、眼睛、手掌、种子、镜子。
“这是……人格具象化?”伊莱娜震惊。
“不。”艾登抚摸其中一棵树干,“这是它们选择了宿主。”
从此,每当某一人格主导意识,对应的水晶树就会亮起,并向周围释放特定频率的安抚波。学生们可以在树下冥想,感受不同心理状态的平衡之美。
然而平静并未持续太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