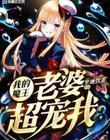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上玉阙 > 第十六章 簸箩会新来了个年轻人1 23W求月票(第1页)
第十六章 簸箩会新来了个年轻人1 23W求月票(第1页)
罗刹妖皇震怒,群仙台上的金丹们都心有戚戚。
一场顶金扩容,怎么还没开始扩,就要‘引爆大天地’了?
而月华,则是若有所思注视着玉阙仙尊的侧脸,心中思绪翻涌,她已经看懂了玉阙仙尊的思路。
。。。
夜雨落于启明城时,总是无声的。
不是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温柔,而是像记忆被悄悄抹去时的静谧??没有雷鸣,没有风啸,只有屋檐滴水的节奏,缓慢得如同梦核跳动。苏明爻坐在老槐树下,膝上摊着那本小女孩送来的手抄册子,纸页已被雨水浸得微皱,字迹晕开如泪痕。她没躲雨,也不觉得冷。三年来,她已习惯在这样的夜里守候,仿佛等待某个注定不会现身的人,或某种尚未成形的答案。
忽然,一片晶莹落在书页上,不是雨。
是一粒从西北方飘来的晶尘,带着遥远回响,在触碰到纸面的瞬间碎裂,释放出一段低语:“……他们说沉默是最深的反抗,可若无人听见,沉默还是反抗吗?”
苏明爻瞳孔微缩。这不是今人的问题,语气苍老,语调中透着青铜时代的锈味。她抬手接住第二粒尘埃,它在掌心融化,化作一句更短的话:“**塔倒了,谁来做梦?**”
她猛地起身,望向西北。那片晶石森林自流星坠落后逐年扩张,如今已绵延百里,白日里看去如霜雪覆盖的山峦,夜晚则泛着幽蓝脉动的光,像是大地深处未愈合的伤口,又像新生的神经末梢。据探者回报,凡是深入其中三日以上者,皆会开始梦见不属于自己的人生:有人梦见自己是远古祭司,主持一场献祭全城的仪式;有人醒来后能用早已失传的语言吟唱哀歌;更有甚者,连续七夜重复同一段梦境??他们在一座倒悬的塔中行走,脚下是天空,头顶是深渊,而每一步都踩碎一个问题。
盲童就是在那个地方消失的。
半年前,他留下一句话:“我要去听最初的提问。”随后走入晶林深处,再未归来。起初人们还派忆者追踪,但所有进入者都会在第三天失去方向感,记忆错乱,甚至分不清自己是谁。最后一名归来的忆者跪在城门前,满脸血泪,嘶声喊道:“我不是我!我是问题本身!”随即昏死,醒后再也无法说话,只用手指不停划动空气,似在书写无形之问。
苏明爻曾想亲自前往,却被百诘庭以“执灯者不可轻涉未知”为由劝阻。她没有争辩,只是默默将一枚刻有自己名字的玉符埋入槐树根下,说:“若有朝一日我迷失了,凭此符唤我回来。”
而现在,晶尘竟主动飞来,且携带着跨越时空的疑问。
这意味着什么?是晶林终于决定与外界对话?还是……某种意识正通过碎片化的语言,试图重建连接?
她收起册子,披上旧斗篷,走向城西马厩。那里拴着一匹从未离鞍的黑马,鬃毛灰白,眼中有星图流转??它是当年从伪塔废墟中自行走出的灵兽,不吃不喝,却始终活着,只认苏明爻一人。她翻身上马,轻声道:“去西北。”
马蹄踏破雨幕,启明城在身后渐成模糊轮廓。沿途村庄皆闭门熄灯,唯有少数人家窗缝透出微光,隐约可见有人伏案疾书,或低声诵问。这些年来,“问”已成为日常仪式,不再需要塔钟召唤。孩子们入学第一课不是识字,而是学会如何提出一个“诚实的问题”。市集上最畅销的不再是丹药法宝,而是空白玉简和忆火引芯。甚至连乞丐也会拦住行人,问一句:“你今天有没有真正困惑过?”
但苏明爻知道,平静之下暗流未止。
北境仍有零星村落自愿焚毁书籍,宣称“无知即安宁”;南疆某些部落重拾旧俗,将质疑者逐出寨子,称其“魂被伪塔附体”;更有传言,第九塔残基之下,每逢月圆之夜仍会传出低语,内容竟是对《问天录》的逐条反驳,逻辑严密,文风冷峻,宛如另一个苏明爻在与自己辩论。
她不信鬼神,却不得不信:**思想一旦生根,便不死不灭。**
第三日黄昏,她抵达晶林边缘。
此处气温骤降,空气中悬浮着无数细小光点,随呼吸进出肺腑,带来轻微刺痛感。地面并非泥土,而是由凝固的记忆结晶铺就,踩上去发出类似骨骼断裂的脆响。远处,晶柱林立,每一根内部都封存着扭曲的人影、破碎的城市、燃烧的经卷,甚至还有正在消亡的星辰影像。
她刚迈出第一步,耳边便响起声音??不是来自外界,而是从颅骨内侧升起:
“你为何而来?”
“你以为你能分辨真实与模仿?”
“如果所有的‘我’都是被他人问题塑造的产物,自由是否只是一个幻觉?”
这些问题如针扎进意识,逼她立刻回应。她停下脚步,闭目答道:“我不知答案。但我愿意承受追问。”
话音落下,前方一条路径悄然浮现,由晶尘汇聚而成,蜿蜒通向森林中心。
走了七日七夜,她未曾进食,也未睡眠,却毫无疲惫之感。相反,她的记忆开始反向流动:童年母亲教她写字的画面突然变得异常清晰;少年时期在伪塔下目睹同伴被拖入地底的尖叫重新刺穿耳膜;甚至十年前焚毁《守瞳誓词》那一刻的火焰温度,此刻都在皮肤上重现。她明白,这不是回忆,而是被晶林读取后投射回现实的“共感”。
第八日清晨,她在一片空地上停下。
中央矗立着一根巨大的透明晶柱,高逾百丈,形状酷似第十塔的缩影。柱中并无人影,唯有一团缓缓旋转的光影,时而凝聚成人形轮廓,时而散作星云状。她走近时,那光影忽然静止,随即传来熟悉的声音:
“你迟到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