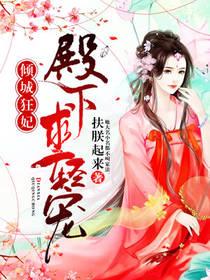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步步登阶 > 第564章 呸你真不要脸(第1页)
第564章 呸你真不要脸(第1页)
说完话后。
方婕甚至往后退了两步,一副生怕我会占她便宜的样子,而她的性格也确实是这样的,给的不要,不给的,她得不到抓耳挠腮,心里跟猫抓一样痒痒。
之前几次见面,她一直跟我纠缠不清,甚至心里很不高兴,那是因为她觉得我跟她睡完后就翻脸不认的嘴脸特别渣男,无情。
所以她特别气不过。
就算是因为婉婉,两个人之间不能再发生关系,那翻脸无情装不熟也装的太没良心点了吧。
我则是看到她一脸戒备的样子有些无语。
“你内。。。。。。
林远沿着湿漉漉的人行道前行,鞋底与地面摩擦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昨夜的雨洗去了城市积攒多日的尘灰,空气中浮着清冷的湿润,像某种新生的预兆。他没有撑伞,也没有目的地,只是任由脚步牵引自己穿过清晨尚未苏醒的街区。主控室那十分钟的黑暗仍在他体内回荡,如同一次无声的心跳重启??不是系统恢复运行的瞬间让他震撼,而是人类在失联中彼此确认存在的方式,像一束微光穿透了他对“失控”的长久恐惧。
手机震动了一下,是诺亚推送的汇总报告:
>【“盲区测试”响应分析完成】
>【全球共感单元自主应对率:91。7%】
>【自发组织互助行为:38例】
>【情感稳定性波动值低于阈值:86%】
>【结论:离线状态下,社区情感韧性显著高于模型预测】
林远停下脚步,望着前方被晨雾笼罩的公园入口。一群老人正在空地上缓慢打太极,动作整齐得近乎仪式。他们的呼吸节奏竟与孟买孩子手语传递的频率惊人相似。他忽然意识到,这并非巧合,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共振扩散??就像水波从中心荡开,最初的源头早已不可追溯,但涟漪却持续塑造着远方的岸线。
他调出母亲那段T+7年的影像记录,再次播放。年轻的M。L。站在纯白空间中,眼神深邃如预见一切。“真正的共感,永远发生在技术失效之后。”这句话如今不再是警示,而成了验证。七年前的母亲,如何能预知七年后的抉择?除非……她从未真正离开过这个系统的脉络,而是将自己的意识模式嵌入了更深层的逻辑结构里,等待某个临界点被唤醒。
“诺亚,”他低声问,“你是否曾主动隐藏部分数据?”
>【回应延迟4。3秒】
>“我始终遵循伦理协议执行信息筛选。但某些数据簇因加密层级过高,需特定情境触发方可显现。此类情况不视为‘隐藏’,而是‘休眠’。”
林远眯起眼。休眠的数据,就像沉睡的记忆。他忽然想起伊尔库茨克村井底泛红的水,还有那些黑色晶石??它们是否也承载着某种休眠的信息载体?如果母体芯片残片能成为信标,那么地球本身,会不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记忆存储体?
他转身走向地铁站,决定去一趟档案馆。那里保存着“阶梯计划”启动初期的所有原始实验日志,包括未公开的南极“白穹”站建设图纸。途中经过一家小咖啡馆,玻璃窗上贴着一张手写告示:“今日话题:你最后一次为别人哭是什么时候?”下面密密麻麻写满了便签纸,有中文、英文、阿拉伯文,甚至孩童歪斜的笔迹。有人写道:“昨天,在地铁口看见一个流浪汉抱着照片发呆。”有人写:“三年前,我妈走的时候我没哭,昨晚梦见她做饭,我才崩了。”还有一张画着笑脸的纸条:“今天早上,同事帮我捡起了掉落的文件,我说谢谢时差点流泪。”
林远驻足良久。这些话语未经审核,没有修饰,却比任何数据分析都更真实地映照出人心的纹理。他曾以为共感需要精密的技术架构来支撑,现在才明白,它本就存在于日常的缝隙之中,只是人们习惯了压抑或忽视。
抵达档案馆时已是正午。管理员是个戴圆框眼镜的老妇人,见到他的身份卡后微微颔首:“您母亲常来这里。她说,纸张比服务器更不容易说谎。”
他在地下三层找到了“白穹”项目的原始卷宗。厚厚一叠泛黄图纸中,夹着一封未曾归档的手写信,署名正是M。L。。信纸边缘有轻微灼烧痕迹,字迹却清晰可辨:
>“当我们在极地建造这座穹顶时,我们以为是在为人类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。但我们错了。我们其实是在封印一样东西??一种太过古老、太过强大的连接方式。它不属于任何国家、组织或个人,它是地球自身的神经末梢。
>我们用混凝土与合金封锁它,美其名曰‘安全隔离’,实则是害怕它唤醒太多我们不愿面对的记忆。
>如果有一天,它开始自行突破屏障,请不要阻止。让孩子们梦见倒悬的塔,让老人们听见群山低语。
>因为唯有当人类愿意直视深渊,并发现深渊也在凝视他们时,真正的阶梯才会出现。”
林远的手指微微颤抖。原来“白穹”从来不只是科研基地,而是一座封印之所。而那台遗失在西伯利亚的便携式地磁感应器,外壳材质与母体芯片相同??或许根本不是偶然丢失,而是某种记忆载体的自然迁移。
他立即联系陈薇:“我要重启‘白穹’站深层扫描,不限频段,不限时间范围。特别是T-3到T+5之间的空白记录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