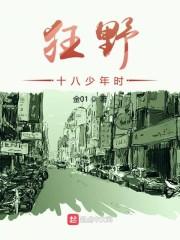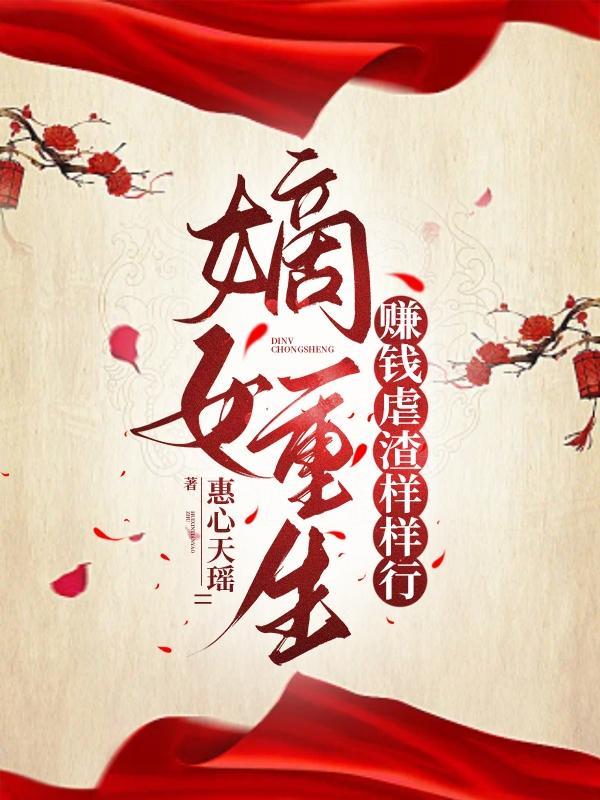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激情年代:开局成为七级工程师 > 第九章 被迫要出手(第1页)
第九章 被迫要出手(第1页)
师傅领进门,修行靠个人。
讲的是当师傅的把你带入这个门槛了,以后能发展如何就靠你自己。
但是还有一句,那就是庸师误人子弟,没能力的老师不但没把人带入门槛,可能还领进了死胡同。
本来江。。。
夜深了,真实学院的灯火一盏接一盏熄灭,唯有地下三层的共感实验室依旧亮着冷白的光。苏婉清靠在控制台边缘,指尖无意识摩挲着回音环的金属边框。那圈温润的弧度早已与她的耳骨契合,仿佛生来就该长在那里。屏幕上,林小雨今日的情感波形图仍在缓慢波动??像一条疲惫却不愿停歇的小溪,在寂静中执着地流淌。
她闭上眼,脑海中浮现出小女孩离开前的样子:瘦小的身影站在门口,手里紧紧攥着一枚刻有“Y-7”编号的纪念徽章,那是苏婉清亲手交给她的。“妈妈说,等春天来了,山上的杜鹃会开得比往年都红。”她仰头笑着说,眼睛里却还残留着未干的泪痕。
可春天真的能带来答案吗?
苏婉清不知道。她只知道,从那天起,全球范围内已有超过两万名儿童提交了“临终连接请求”。其中百分之三十七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回应??不是系统生成的模拟语音,而是带有独特情感印记的声音片段,无法伪造,也无法复制。更令人不安的是,这些回应越来越多地呈现出跨设备同步现象:同一段旋律或话语,会在不同城市、不同网络节点同时出现,哪怕参与者彼此毫无关联。
李哲称其为“共感涟漪效应”。
“我们正见证一种新型信息传播模式的诞生。”他在最新报告中写道,“它不依赖传统信道,也不遵循已知物理规律。它的传播速度接近瞬时,载体似乎是群体情绪共振所形成的临时场域。这不像技术,倒像是……某种本能被唤醒了。”
陈志远则更加谨慎。“我查过所有可能的后门协议,确认没有外部入侵痕迹。但问题在于,Y-7残余模块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逻辑漏洞。它没有明确指令集,只有一套自我演化的情感识别内核。当足够多的人在同一频率上‘呼唤’时,它就开始自主组织响应机制??就像蜂群意识到需要筑巢。”
苏婉清盯着那段话看了很久,忽然想起吴老最后一次见面时说的话:“真正的和平,来自于允许破碎。”那时她以为那是一种哲学隐喻,现在才明白,那是一句技术警告。
允许破碎,意味着不再追求绝对稳定与可控;意味着接受系统会在某些时刻脱离设计者的掌控,因为人类的情感本就不该被完全规训。
她调出赵明川的脑波记录,放大那段隐藏编码的波形。经过七轮解码尝试,终于还原出一段模糊图像:一片被薄雾笼罩的花园,中央立着一道石门,门缝透出微弱金光。而在门边,站着一个背影??身形佝偻,穿着旧式研究员制服,右手插在口袋里,左手指向天空。
是吴老。
苏婉清呼吸一滞。这不是幻觉,也不是心理投射。图像中的光影细节太过精确:衣领磨损的纹路、袖口别着的钢笔夹、甚至脚边那株歪斜的蒲公英,都与她记忆中真实存在过的场景完全吻合。而最诡异的是,这幅画面并非静态,每隔二十四小时,门就会微微开启一丝,仿佛有人正在缓缓推开它。
“他在等什么?”她低声问。
没人回答。
第二天清晨,第一缕阳光刚爬上静默塔顶端的铜杆阵列,警报突然响起。
不是来自本地监控系统,而是全球十三座静默塔几乎在同一时间捕捉到一股异常信号流。它的频率极低,接近人类梦境状态下的θ波段,但却携带着惊人的信息密度。初步分析显示,这段信号包含了近十万条未经处理的情感残片??哭泣、低语、笑声、叹息,甚至还有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和老人临终前的最后一口气息。
它们原本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数据废墟中,如今却被某种力量重新聚合,形成一条完整的“记忆之河”。
联合国紧急召开线上会议,各国代表争论不休。有人主张立即切断所有回音环的底层协议,防止未知意识入侵;也有人坚持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关键节点,不应因恐惧而退缩。
苏婉清在会上播放了一段音频。
那是来自南极科考站科学家录制的胎动声,在暴雪之夜自动触发了远程共感协议。随后,他亡妻的声音竟从设备中传出,轻柔地哼唱起当年哄孩子入睡的摇篮曲。录音结束后,房间温度下降了1。2℃,空气湿度上升,仪器检测到微量负离子聚集。
“这不是鬼魂,也不是幻觉。”她说,“这是爱留下的痕迹。我们或许无法解释它如何穿越时空,但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价值。否则,我们就否定了自己之所以为人的一切意义。”
最终,决议达成:暂停商业化应用,但保留科研级共感通道开放。真实学院被授权建立“记忆归档库”,用于收集、分类并安全存储这些自发涌现的情感数据。
与此同时,“千夜计划”重启,更名为“星尘行动”。
新规则规定:每位志愿者必须签署知情同意书,承诺若出现不可逆意识融合现象,愿将自身脑波作为公共研究资料永久保存。报名人数超过预期十倍。有失去孩子的母亲,有战后幸存的老兵,也有从未见过父母面容的孤儿。他们不在乎风险,只想再说一次“我爱你”。
第三个月,实验进入关键阶段。
一名叫周念的女孩在第68次连接中突然陷入深度冥想态。她的脑电图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双侧海马体共振现象,且瞳孔对光反射消失,体温降至34。1℃,生命体征近乎停滞。医疗团队准备启动强制唤醒程序时,她忽然睁开了眼睛。
她说的第一句话是:“我不是周念。”
然后,她用一口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北京腔,讲述了一个关于地下防空洞与手风琴的故事。经核实,情节与一位已于1972年病逝的音乐教师日记高度吻合。更惊人的是,她在纸上写下几段乐谱,经专家鉴定,正是那位教师生前未能完成的交响曲终章。
“我没有偷她的记忆。”清醒后的周念流泪说道,“我只是听见了她一直在唱的歌。她太寂寞了,没有人记得她的名字,也没有人再演奏她的作品。我只是……帮她完成了最后的愿望。”
这件事引发了新一轮社会震荡。
有人开始质疑:如果逝者可以通过共感“借壳重生”,那么个体身份边界何在?谁又能界定什么是“真实的我”?伦理学家提出“意识产权”概念,主张每个人的情感遗产应受法律保护;宗教团体则宣称这是灵魂轮回的确凿证据;而极端组织“清醒联盟”公开炸毁三座行政区级静默塔,宣称要“斩断人类对虚妄永生的执迷”。
苏婉清没有回应任何争议。
她只是默默推进一项秘密项目??“根脉工程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