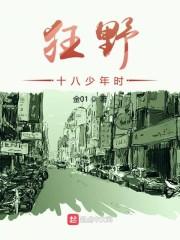书迷阁>自由和枷锁 > 戳穿他们的谎言(第2页)
戳穿他们的谎言(第2页)
成山下了接连几天的大雨,似乎是老天爷替洛言即将失去心爱之人难过一样,好不容易放了晴,却起了一层浓雾。
常吃的那家早餐店也没开门,洛言随便在路边买了两份油条就回了家,陈默还没起来。
从那日过后,陈默就非常嗜睡,好像要把这十几年没睡的时间,都补上。
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,撒在柏油马路上的斑斑点点,一部分也撒在了实验楼的墙壁上。
洛言拉着陈默的手,踩着那些明亮的光点,像踩在钢琴的黑白键一样。
这条宿舍到实验楼的路,食堂到图书馆的路,他们走了不下百次。
陈默总是在图书馆二楼的靠窗的位置占两个座位。洛言总是在图书馆容易犯困,陈默多次劝过他,不用陪着自己,,洛言每次都答应,但每次都会去!
今天,陈默像往常一样,歪着头看着洛言撑着头,闭着眼睛,嘴唇微微张开,然后脑袋像脱力一般一点一点的歪向旁边。这时候,陈默总是会伸出手,轻轻的把他的头按在自己的肩膀上,让他靠着会睡的舒服一点。
早上刚洗过的蓬松的头发,带着一丝浓郁的茉莉花香味,伴随着洛言均匀的呼吸声,陈默手机里有很多洛言的呼吸声录音,他觉得那是这个世界上最动听的乐章。偶尔洛言醒来,桌子上还会放着一杯他喜欢喝的葡萄汁和一张画着笑脸的便签。
——买点吃的,一会儿回来!
周末的傍晚,实验楼顶就是他们的秘密基地。
那里能看到整片天空从湛蓝渐变成橘红,再沉入静谧的紫。
有一次,洛言穿着一个破了洞的长衫,抱着一本书,还特意把发型做成了鲁迅头发的模样,一手背后,嘴唇上还粘了黑胡子。
拿出手机非得让陈默给他录一段。
陈默靠在实验楼顶的门上,稳稳的把手机对着前方的洛言。
洛言理了理衣襟,清理了一下嗓音,摆出了鲁迅的姿态“拍了吗?”
陈默点点头“拍了!”
洛言从兜里掏出一张纸,身影在镜头里来回走动,偶尔指指天,踏踏地。
那鲁迅风格的嗓音一出口,整个人身上,瞬间镀上了一层看不透的忧伤:
阿默:
近日重读《野草》,见那地火在黑暗中奔突,脑海中想的竟然是你。我素来不信什么圆满,总觉得这世间充斥这未完成的石膏雕像,处处都是粗粝的棱角。偏生遇见你,倒像是在长夜漫漫里寻着一盏不必明亮,却始终温这的油灯。
他们都道我冷硬如未开刃的古刀,唯独你,立在黄昏的影里,看我锈迹下未凝结的铁浆。
我们原是两册残卷,被风雨打湿了封皮,却在对方的缺页处,读出了完整的章句。
江南的梅雨又至,瓦当滴答着,倒像是在敲着摩斯密码。我大概是听出了思念的味道。
我坐在窗前蘸墨,忽然觉得,这笔画,横竖间,都成了寄不出的信礼。
也罢,横竖我们都是不肯轻易交出底稿的人,倒不如学习那两株枣树,只管在萧瑟里站着——你的根须缠住我的,我的树影覆上你的,如此这般,便可抵得过万千甜腻的誓言。
夜已深,茶也凉了半盏。这荒唐的笔墨你且看着,若觉得可笑,便揉作纸团,扔进废纸娄里。
最后镜头里的那张脸,在陈默的面前无限放大,洛言是笑着的,可他觉得那笑容无比讽刺。
洛言站在栏杆处,说“到底我们这类人,连剖白心迹都要带着讽刺的壳!”
陈默点点头,笑的苍白又荒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