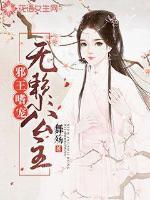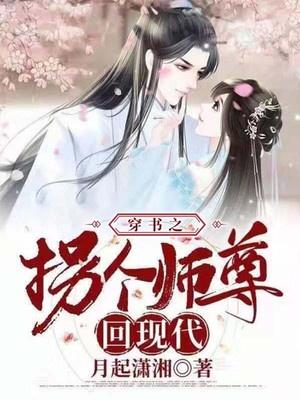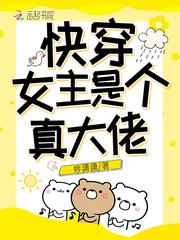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状元郎 > 第三一三章 发配(第2页)
第三一三章 发配(第2页)
掌声雷动,热泪纵横。
然而,风暴并未停歇。
半月后,京城传来消息:内阁以“程序不合”为由,驳回浙江推行女子旁听之请,勒令立即停止,并严查“擅自扩大教育权限”责任人。同时,刑部派出御史团,将以“整顿地方财政”名义南下巡查,首站便是杭州。
苏录知道,真正的对决开始了。
他在日记中写道:
>“他们不怕贪官,因为贪官可用;他们不怕庸官,因为庸官听话。但他们怕清官能干,怕理想者清醒,怕有人既能洞察体制之弊,又有勇气破局而出。所以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”
>
>“我本无意为英雄,奈何时代逼人挺身。既然如此,那就让他们看看,一个穷小子的骨头,到底有多硬。”
面对朝廷压力,周延儒决定兵行险招??奏请皇帝亲派钦差,而非依赖刑部御史。他在奏折中直言:“臣之所行,皆依圣贤之道,合祖制本意。然地方积弊已久,牵连甚广,若由刑部自查,恐同气连枝,反成包庇。唯有天子耳目,方可秉公决断。”
与此同时,苏录秘密联络省内数十位开明士绅、退休老臣,请他们在京子弟联名上书,呼吁“教育乃国本,不宜因噎废食”。他又发动各地学子撰写《劝学陈情表》,以朴实语言讲述寒门求学之艰,汇集成册,题曰《万家灯火书》,托商队暗中送往京城各大书院与翰林院。
一场无声的舆论战,在千里之外悄然打响。
冬至前夕,钦差终于抵达杭州。来者非他人,竟是当朝礼部侍郎、太子讲官杨廷和之子杨慎,年不过三十,却以刚直闻名。他未入住官驿,而是径赴清源局查阅原始档案,连续三日闭门审阅,不接宴请,不受馈赠。
第四日,他召见苏录。
“你就是那个敢对巡抚说‘若偏离正道必直言劝谏’的苏解元?”
“正是晚生。”
杨慎盯着他看了许久,忽然问:“你觉得,什么是真正的教育?”
苏录略一思索,答道:“教育,是让一个放牛的孩子,也能读懂诗经;是让一个渔家女儿,不必男装也能入学;是让天下人相信,出身不能决定智慧,贫穷不应剥夺希望。它不是筛选贵族的筛子,而是点亮众生的火把。”
杨慎动容,起身离座,亲自为他斟茶:“好一句‘点亮众生的火把’。我在京中读过你们的《万家灯火书》,有个绍兴女孩写道:‘我娘说女子读书无用,可我想知道,为什么月亮会圆又缺?’你知道吗?我看到这句话时,哭了。”
他放下茶盏,语气转肃:“我奉旨而来,原以为浙江狂悖妄为。如今看来,错不在你们,而在庙堂之上,太多人忘了读书的初心。”
临行前,他对周延儒说:“我会如实禀报陛下。但你要记住,政治如棋,一步不慎,满盘皆输。下次改革,务必先争‘名分’,再行实事。否则,纵有千般道理,也会被一句‘违制’压死。”
一个月后,圣旨下达:
“浙江试行新式乡学制,为期三年,成效显著者,推广全国。其余争议条款,交由礼部会同六部共议。”
虽未全胜,却是胜利的开端。
春风再起时,杭州第一所公立女子学堂正式开学。三百名女孩穿着统一蓝布裙衫,整齐列队,齐声诵读《千字文》。苏录站在台下,望着她们稚嫩而坚定的脸庞,忽然想起幼年干娘的话:“孩子,你要替那些读不起书的人,把书念下去。”
他眼角湿润,却笑了。
当晚,他又收到一封匿名信,这次只有短短一句:
“小心身边人,灯下最黑处。”
他怔住良久,目光扫过书房每一个角落。烛光摇曳,映出墙上父亲画像的阴影,恰好遮住了自己的半边脸。
他知道,这场战争远未结束。
权力的棋盘上,每一步都踩着人心的裂缝。
但他也明白,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渴望光明,他就不能停下脚步。
窗外,春雷隐隐,万物复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