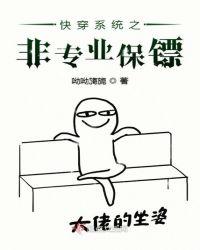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状元郎 > 第三二二章 苏录的企图(第1页)
第三二二章 苏录的企图(第1页)
安贵荣送来的大量生活物资,大大改善了龙场驿的生活条件。
王守仁的窗户上贴上了厚厚的窗纸,不用再担心风雨进屋了。
屋里竹床上,挂起了蚊帐,铺上了崭新的棉布被褥,再也不用裹着毡子睡草席子了。。。。
夜雨如注,陈砚之立于父亲墓前,火光渐熄,余烬随风飘散。他未撑伞,任雨水顺着发梢滴落,浸透衣袍。身后石碑上“忠贞文正”四字在闪电照耀下泛着冷光,仿佛天地也为之动容。良久,他缓缓跪下,三叩首,起身离去。
归途泥泞,马蹄深陷。他策马穿城而过,街巷空寂,唯闻更鼓断续。然行至宣阳坊口,忽见数道黑影伏于屋脊,弓弦微响。他猛然勒马,一支羽箭擦颊而过,钉入树干,尾羽犹颤。
“躲!”一声低喝自暗处传来,一人疾扑而出,将他拽下马背。是李三,脸上带伤,气息急促。“大人快走!他们不止一波,东、西、北三面皆有埋伏。”
陈砚之迅速起身:“你怎在此?”
“徐大人派我来接应。”李三喘息道,“今晨大理寺狱中传出消息,林景行昨夜以金簪刺喉,未死,只断声带。今午便有旨意,称其‘病重不宜羁押’,拟移送私宅监禁。徐大人恐其中有诈,命我提醒您提防反扑。”
陈砚之瞳孔骤缩。移送私宅?分明是要放虎归山!
他立即调转马头,直奔刑部。然未及城门,前方火把如龙,禁军列阵封锁要道。旗号非朝廷制式,而是赵元弼旧部标记。陈砚之心中一沉??这些人本应已被收编,如今竟仍听命于败党?
“绕道水门!”他对李三低语,“你去通知徐正言,就说林氏残党图谋劫囚,极可能已在宫中安插内应。让他立刻进宫面圣!”
李三点头,翻墙而去。
陈砚之独自潜行,借河道芦苇掩护,从废弃的漕渠暗闸摸入皇城外郭。此处原为前朝排水沟,年久失修,臭气熏天,却无人看守。他攀爬铁网时手掌被锈钩划破,鲜血直流,却不敢停歇。
终于抵达文渊阁侧门,此处毗邻内阁值房,亦是皇帝批阅奏章常经之地。他贴墙蹲伏,忽听廊下脚步轻响,一名小太监提灯而来,神色慌张。待其走近,陈砚之闪身而出,捂住其口,低声问:“王德全可在?”
小太监惊恐摇头,指了指乾清宫方向,又比划割喉手势。
陈砚之心下一凛:王德全出事了?
正欲再问,远处钟鼓齐鸣??竟是早朝钟声提前响起!
不对。此时不过寅末,距常例早朝尚差半个时辰。除非……有紧急军情或政变!
他冒险沿檐角潜行至乾清宫后窗,透过纸糊缝隙窥视殿内。只见皇帝端坐龙椅,面色凝重;林景行竟赫然立于阶下,虽颈缠白布,不能言语,却手持一份黄绫诏书,由身旁一名紫袍老臣代读。
那老臣声音苍老却威严:“……今查新科状元陈砚之,勾结废员徐正言,伪造证据,构陷大臣,煽动舆情,动摇国本。其所呈残片文书,乃三十年前御史台焚毁旧档之余烬,如何能证今日之冤?显系蓄意欺君。朕念其年少无知,暂免死罪,革去功名,贬为庶民,流放琼州!”
陈砚之浑身剧震,几乎撞响窗棂。
这是伪诏!
他亲眼所见皇帝亲允平反,岂会一夜之间翻案?更何况,流放诏书须经内阁副署、司礼监用印,方为有效。而此刻王德全不见踪影,玉玺何在?此诏必是矫造!
他咬牙退后,思索对策。若此刻现身抗辩,无异自投罗网。必须找到真凭实据,揭穿这场阴谋。
他悄然折返文渊阁,这里是国家典籍中枢,藏有历年诏令底稿与印鉴登记簿。若能查到今日诏书未录档,便可证明其非法。
幸而守阁老吏是他昔日同窗,虽不知详情,见他狼狈模样,仍冒险放行。陈砚之直奔“诏敕类”架阁,翻找今晨记录。果然,空白无载。他又查阅玉玺使用登记,昨日申时三刻后便无签字,而王德全惯例每日必亲自登记。
证据确凿。
但他刚合上册子,门外已传来甲胄碰撞之声。有人高喊:“搜!陈砚之擅闯禁地,图谋不轨!”
他迅速将册子塞入怀中,翻窗跃入后园假山洞穴。追兵涌入阁内,火把映得书架通明。他在黑暗中蜷缩,听见领头者冷笑:“奉林相爷令,凡接触过陈砚之者,一律拘押审问。格杀勿论。”
林相爷?林景行已被罢官,何来“相爷”之称?
寒意自脊背升起。对方不仅掌控了部分禁军,竟连宫廷礼仪称谓都敢擅自更改。这已非简单翻案,而是赤裸裸的政变预演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