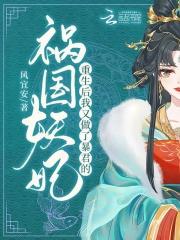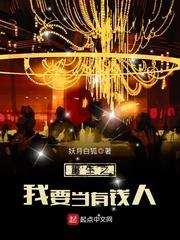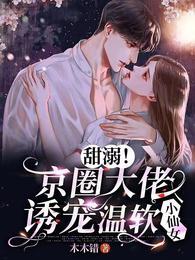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稚御山河 > 第三十五回 供词字字藏机锋 暗探句句露端倪(第1页)
第三十五回 供词字字藏机锋 暗探句句露端倪(第1页)
回前诗
巧舌织网覆公堂,暗卷横飞破伪装。
不是齐王不深究,只留后手待风狂。
翌日,大理寺正堂内寒气森森,案几后并排坐着三位主审——齐王居中,朱启建与钱为业分坐两侧,皆是面色沉凝。堂下两侧站满了持械衙役,气氛肃穆得连呼吸都透着滞重。齐王拿起案上的卷宗轻轻一叩,沉声道:“传张翠喜。”
片刻后,帘幕轻掀,张翠喜缓步走入堂中。她依旧是一身素净衣裙,未施粉黛的脸上不见半分慌乱,唯有眼底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警惕。走到堂中,她依着规矩缓缓跪拜,动作从容不迫,没有寻常女子的瑟缩。
“起来吧。”齐王的声音不高,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,“今日问你之事,需如实作答,半句虚言,休怪律法无情。”
张翠喜缓缓起身,垂眸而立,声音轻柔却清晰:“奴家晓得,定当知无不言。”
齐王目光落在她身上,缓缓开口:“你与桂宁侯是如何相识的?他待你如何?”
张翠喜抬眸略作思索,随即垂眸答道:“奴家与桂宁侯相识于暖乐楼。彼时侯爷偶至楼中听曲,奴家忝为乐伎,不过是依着规矩弹唱侍奉,并无特殊交情。侯爷待奴家,亦只是寻常宾客对乐伎的礼数,未曾有过逾矩之举,更无格外厚待之处。”她语气平淡,仿佛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旧事,既不刻意攀附,也不刻意疏远。
齐王微微颔首,又问:“那你又是如何结交杜之贵的?他为何会斥资三万两为你赎身?”
这话一出,堂下的衙役们都下意识地屏住了呼吸,连钱为业的手指都微微动了动。张翠喜却依旧镇定,她轻轻福了福身,道:“杜大人初识奴家,也是在暖乐楼。他说欣赏奴家的曲艺,不忍奴家困于风月场中,便提出为奴家赎身。至于那三万两,奴家虽知晓数额巨大,却也只是杜大人一片怜惜之意,奴家未曾主动求过,也不知他为何愿出这般重金。想来,许是杜大人素来仁善,见不得女子受困吧。”
她的话滴水不漏,将所有关联都推给了“听曲”“怜惜”这些模糊的由头,既承认了相识与赎身之事,又巧妙地避开了任何涉及权贵勾结、利益交换的痕迹。语气里那份恰到好处的谦卑与懵懂,让人挑不出半分错处,仿佛她真的只是个被动接受命运安排的弱女子,对背后的暗流涌动一无所知。
齐王盯着她看了片刻,见她始终垂眸敛目,神色坦然,一时竟也无从追问。齐王目光扫过两侧,沉声道:“二位大人可有要问的?”
钱为业闻言,悄悄松了口气——方才张翠喜那番说辞虽看似无懈可击,却总让他觉得藏着猫腻,此刻正好借问话探探底细。他身子微微前倾,指尖叩了叩案面,语气带着几分刻意的温和:“张翠喜,老夫再问你,杜之贵为你赎身后,可有对你提过什么要求?或是让你做过什么事?”
张翠喜垂眸思忖片刻,轻声答道:“杜大人赎身之后,只说让奴家安心休养,不必再操持乐伎生计。他偶尔会来探望,也只是闲谈几句曲艺,从未提过任何要求,更未曾让奴家做过什么不合规矩的事。”她话音一顿,似是想起了什么,又补充道,“倒是奴家过意不去,曾想为杜大人弹曲解闷,他却说不必拘礼,让奴家自在便好。”
钱为业眉头微蹙,又追问道:“那你与桂宁侯在暖乐楼相识后,他可有私下约见过你?或是托人给你带过什么东西?”
“不曾有过。”张翠喜答得干脆,却又留了几分余地,“侯爷虽偶尔去暖乐楼,但多是与同僚一同,听曲之后便离去,从未私下约见。至于带东西,更是没有——奴家不过是个乐伎,怎敢劳烦侯爷这般费心。”
钱为业眯起眼睛,语气陡然沉了些:“你这话当真?要知道,此刻说谎,可不是闹着玩的!”
张翠喜抬起头,眼底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委屈,却依旧从容:“奴家不敢欺瞒大人。侯爷身份尊贵,奴家深知自己的斤两,怎敢攀附?若是真有私下往来,此刻也不敢隐瞒——毕竟律法在前,奴家岂敢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?”
她的话依旧滴水不漏,既回应了问题,又借着“身份悬殊”“不敢攀附”的由头堵住了后续追问的可能。钱为业接连问了几句,从赎身后的行踪到与桂宁侯的交集,张翠喜始终应对得从容不迫,语气或谦卑或委屈,却偏偏不露出半点破绽,仿佛真的只是个置身事外的局中人。
钱为业心中暗恼,却也不得不承认,这女子的心思之缜密,口舌之伶俐,远超寻常风月场中人。他看向齐王,轻轻摇了摇头——再问下去,恐怕也问不出什么名堂。朱启建手指摩挲着案上的惊堂木,目光落在张翠喜身上,语气听似平和,实则藏着为桂宁侯开脱的心思:“张翠喜,老夫问你,你在城阳郡暖乐楼时,曲艺也算有名,若真有人疼惜,为何偏偏是杜之贵出面为你赎身?城阳郡本地难道就没有愿帮你脱离风月场的人?”
这话看似在追问赎身人的选择,实则在暗示:杜之贵是“偶然”出手,而非与桂宁侯有勾结,毕竟若本地有人愿帮,反倒能坐实桂宁侯“未插手”的清白。
张翠喜瞬间领会到话外之音,垂眸时眼底闪过一丝清明,随即换上怅然神色:“大人有所不知,城阳郡虽有听曲的常客夸过奴家,但多是些寻常商户或读书人,哪有三万两重金为一介乐伎赎身的魄力?再者,暖乐楼楼主待奴家不算苛刻,奴家也从未主动求过赎身,只当会在楼里了此残生。”
她抬眸时,眼底带着几分恰到好处的茫然:“至于杜大人,他当时恰在城阳郡公干,偶然到暖乐楼听曲,说怜我身世可怜,便提出赎身。奴家至今也觉得意外,许是杜大人本就仁善,见不得女子受困吧,奴家实在不知他为何会对我这般费心。”
这番话既回应了“为何是杜之贵”的疑问,又将赎身归为“偶然怜惜”,顺着朱启建的话头弱化了与桂宁侯的关联,依旧保持着“懵懂不知情”的姿态,让人挑不出破绽。
朱启建暗暗点头,面上仍端着公正神色:“如此说来,你与桂宁侯在城阳郡的交集,当真只是‘听曲’这般寻常?”
“确是寻常。”张翠喜垂眸应道,声音轻柔却笃定,“奴家身份低微,能得侯爷赏脸听曲已是万幸,怎敢有半分攀附之心,更谈不上什么特殊纠葛。”
齐王面色沉如水,目光扫过张翠喜,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威严:“张翠喜,今日你所言,可要句句属实。若有半分掺假,他日定罪,可不是寻常责罚能了结的。”
他转头看向堂下记录的书吏,沉声问道:“来人,她的供词都记录在案了吗?”
书吏连忙起身躬身,双手捧着记录册回道:“回王爷,已一字一句记录在案。”
“既如此,”齐王点头,指了指书吏手中的册子,“让她画押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