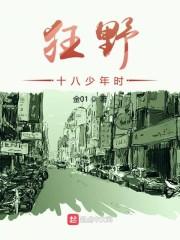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本城主纳个太子妃又何妨 > 意气(第2页)
意气(第2页)
事实清楚,诉求明确,李海道想再打太极已是无处着力。但他心中自有盘算:要在大通建临时战俘安置?眼下虽才几百人,鬼知道后续还有多少?毕竟大景与北狄打了这么多年战。这个无底洞,朝廷不批不补,凭什么他青州府来填这个坑?
他皮笑肉不笑,叹了口气,故作为难道:“辛大人啊,事发突然,你的难处,本官感同身受……但想必你也知,州府拨款有严格的章程,也不是能想拨就拨的,申请、立项、预算审核、逐级报备、批复、出库……环环相扣,都需要时间。本官纵有相助之心,亦无即刻拨款之权啊!”
辛师早有预料,问题的根源还在朝廷。可眼下人已至城下,火烧眉毛了,能救这近火的,只有这储备更丰厚的青州府了。
“大人的难处,辛某明白。”辛师语气平静,没有急切争辩劝说之意,似乎只是在陈述一个毫不相关的事实,“这件事,办好了,朝廷未必会有嘉奖;办砸了,是我辛师‘治城不力’,您也大可置身事外。”
李海道闻言一怔,他没想到辛师这么直白,一语道破,一时无言以对,就连从见到她起就默不作声的齐氏也看过来。
“可是大人,你我不仅是朝廷的命官,更是万千百姓的父母官。”
“而那些战俘,他们曾是我大景的将士,更是大景的英雄,没有他们誓死保护边疆,何来我大通城的安稳?何来您这青州府的繁华?何来千千万万百姓的安居乐业?如今,英雄历劫归来,我们这些所谓的‘父母官’,却要令他们有国不能回,有家不能归吗?若真如此,百姓们会如何看待我们?史笔如刀,后世又会如何评说?!”
辛师眼神如剑,锋芒毕露,一字一句,震得李海道心口发麻,几乎不敢与之直视。
“大人,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,您未必不懂。钱财乃是死物,今日耗去,明日或可再得。但人心若是散了,失了民心士气,再想凝聚,堪比登天。”
“是放眼长远,护我大景军心民心,还是只图眼前省事,固守那几库银钱……大人,您再好好想想,当初你我到底是为何为官!”
李海道如遭雷击,僵立原地。
当年,他亦是三尺笔墨就敢在朝堂上畅所欲言,渴望着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的意气书生,不知从何时起,那些圣贤名言在觥筹交错中化成一杯杯穿肠酒水,那些往日豪情在日复一日的公文里消磨殆尽……
李海道一阵恍惚,在辛师清澈而锐利的眼神中,他仿佛透过时光,看到了过去的自己。
而那……仿佛已是上辈子的事了。
齐氏忽然开口了,她眼眶似有泪水溢出,声线娇柔而微颤:“李海道,你莫忘了,我父亲也是为大景战死的将士之一。”
“若是他还活着,你是不是也要像这般,把我父亲拒于大景国门之外,不闻不问,任其自生自灭?!”
“哎不是……哎夫人!我当然不会!!”李海道额头沁出汗水,苦着脸急忙辩解。
“那不就对了?”齐氏忽的收回眼泪,面无表情,“这些活着回来的将士,与我父亲当年,又有何不同?!不都是为我大景流过血、拼过命的人吗?!”
李海道被问住了,呐呐不能成言。
辛师向收放自如的齐淑慎投去视线,两人视线交汇一瞬,齐淑慎冷哼一声,先行移开视线,侧过身去,只留给辛师一个微红的耳廓。
辛师心下失笑,看着她那倔强的侧影,忽然想起了九年前,那个马背上被吓红了眼,却还执拗抓着金羽花不肯松手的小姑娘。
原来,时光已悄然流逝了这么久。
李海道纠结再三,看着眼前的妻子,再看向目光平静的辛师,两人皆是女子,而两人所言,却令他一个堂堂男儿汗颜。
他终是一声长叹,妥协开口:“罢了……州府库存也非取之不尽,此事终归还需朝廷尽快定夺……现在大通城外安置,所需物资人力,具体数额几何?”
辛师心下一松,与李海道报了个预估数额,李海道点点头,又皱眉道:“此预算……若是第二批、第三批战俘近日抵达,怕是捉襟见肘,本官还需……”
李海道正欲唤来属官清点府库,却忽听门外唱喏声响起——
“青北转运司公文到——”
只见两名身着漕司服饰的差役,捧着盖有转运使朱印的文书走进来,躬身道:
“转运使大人有令,此乃关于边城战俘安置拨款的指令,需知府大人亲阅后即刻回函。”
转运司?
辛师心念电转,按脚程计算,她的加急奏折此刻应尚未抵达京师,转运司怎会在这个节骨眼上送来公文?
辛师右眼皮狂跳。
李海道也一头雾水,接过公文打开,越看越心惊。
辛师觑着李海道阴晴不定的脸色,心道不好。果然,李海道缓缓合上公文,面露难色,摇头叹道:
“辛大人,实在是计划不如变化……此事转运司已接手,本官……已无调度州府应急物资的权限。”
他抬起头,目光复杂地看向辛师,做出了送客的手势:
“辛大人,请回吧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