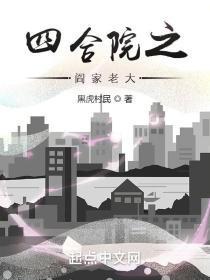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权谋帝王心 > 第4章(第2页)
第4章(第2页)
他将册页小心取出,轻轻拂去灰尘,然后根据年份和事项类型,逐一浏览、分类。
动作依旧不急不缓,带着一种令人心静的专注。阳光透过窗格,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,也照亮他低垂的侧脸和纤细脖颈上那道刺青。
他看得很快,手指有时会在一行字上微微停顿,随即又快速翻过。
萧彻原本在看一份北境传来的密报,目光却不自觉被那边的动静吸引。
他看着那个灰衣少年蹲在箱笼边,几乎被故纸堆淹没。
那副认真的模样,不像是在整理废物,倒像是在沙中淘金。
偶尔看到某些内容时,他那过于苍白的脸上,眉头会极轻地蹙一下,或是唇角无意识地微微抿紧。
那些细微的表情变化,快得如同涟漪,转瞬即逝,却莫名地勾人探究。
“有什么发现?”萧彻忽然开口,打破了书房里长久的寂静。
楚玉衡似乎被惊了一下,抬起头,眼神有一瞬间的恍惚,随即立刻垂下,恭敬道:“回世子,多是些天晟初年与朔州关于粮草、军械交接的旧录,格式冗杂,数字琐碎,并无太多……呃,并无可用于当下的要务。”
他的回答谨慎而妥帖,完全符合一个罪奴该有的认知。
但萧彻却站起身,踱步过去。高大的阴影笼罩下来,楚玉衡下意识地缩了缩肩膀。
萧彻随手从他已经分好的一摞文书里抽出一本,翻了几页。
确实是些枯燥的流水账。
他又看向楚玉衡刚刚正在看的那一本,封皮上写着《元嘉十一年朔州铁料收支录》。
他注意到,楚玉衡方才拂过这一页的手指,无意识地蜷缩了一下。
萧彻目光扫过那泛黄的纸页。上面记录着当年由工部核准,拨给朔州军械局的一批精铁数目、批次及运输记录。
一切都看似正常。
但萧彻的指尖在某一项记录上点了点,那是记录押运官员姓名的地方,墨迹似乎比旁边略深一点,像是后来添补上去的。
“这个押运官,”萧彻状似无意地开口,“王弼?没听说过。元嘉十一年……那会儿北境不太平,路上匪患甚重,能平安押到,倒也算有点本事。”
楚玉衡的身体几不可察地僵了一瞬。
他当然知道元嘉十一年。
那一年,江南漕运也曾发生过一起不大不小的“劫案”,丢失了一批上贡的锦缎。
而当时负责协办江南漕运押送的一名低级官员,好像……也姓王。一个微不足道的巧合,几乎无人注意。
但此刻被萧彻用这种平淡的语气提起,却像一根细针,猝不及防地刺入他严密防守的心防。
他强迫自己呼吸平稳,头垂得更低,声音没有任何波澜:“世子明鉴,奴……不知这些。”
萧彻放下册子,目光落在他发顶,那里有一个小小的发旋。
“是么。”他语气平淡,听不出信还是不信,“看来真是些无用之物。收拾完就搬去库房吧。”
“是。”楚玉衡低声应道。
萧彻回到书案后,重新拿起那份密报,却有些心不在焉。
他方才看得分明,在他提到“匪患”和“王弼”这个名字时,楚玉衡那双总是掩藏在长睫下的眼睛里,骤然闪过了一丝极锐利的光,虽然只有一瞬,却像冰层下的暗流,汹涌而冰冷。
那绝不是一個對過往毫無牽掛、安心認命的罪奴該有的眼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