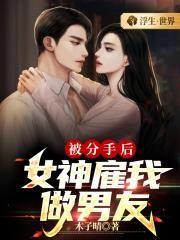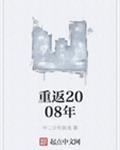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权谋帝王心 > 第54章(第2页)
第54章(第2页)
他看着眼前这一站一立的两个年轻人,一个是他寄予厚望、已然能独当一面的儿子,一个是智谋深远、心性坚韧的未来……萧远山心中长久以来因伤病和局势而积压的阴郁,在此刻一扫而空。
他仿佛看到了北境萧氏更加广阔的未来。
“都不必过谦了。”萧远山脸上露出了罕见的、真正舒心的笑容,虽然浅淡,却驱散了他眉宇间多年的沉疴暮气,“经此一役,朝廷短时间内当无力再犯。我朔州,总算争得了这喘息之机!此乃天大的喜事!”
他看向萧彻,语气恢复了平日的沉稳,却带着更深的托付:“彻儿,后续的安抚、赏赐、军备整顿,你要亲自抓好,务必做到公允,不负军民此番血战之功。”
“儿臣遵命!”萧彻肃然应道。
萧远山又对楚玉衡温和道:“你身子还需静养,切莫再过度劳心。往后,这朔州的大小事务,恐怕还要多倚重你的才智。”
这话,几乎等同于正式认可了楚玉衡在朔州决策层中的地位。
楚玉衡心中微暖,再次躬身:“玉衡定当尽力。”
阳光正好,洒在院中三人身上。
曾经的危机与阴霾渐渐散去,一种新的、充满希望的格局,正在这北境的王府之中,悄然奠定。
朔州王萧远山看着眼前的儿子和这位惊才绝艳的年轻人,只觉得胸中块垒尽去,王心甚慰。
第88章文心北顾
就在朔州城上下沉浸在击退朝廷大军、疫情得控的双重喜悦中,忙于休养生息之时,几辆风尘仆仆、甚至有些破旧的马车,在几个同样面带疲惫、却眼神坚定的仆人护卫下,艰难地驶入了朔州地界。
车上坐着的,正是以李崇文、张士珩为首的那几位,最终下定决心离开京城的文臣士子。
他们的北迁之路,远比想象中更为艰难曲折。
为了避开朝廷可能的耳目和沿途盘查,他们不敢走官道大路,只能选择迂回曲折、人烟稀少的小路乃至荒野。
沿途所见,触目惊心。
越往北,曾经富庶的中原大地越是荒凉。村庄十室九空,田地大片荒芜,龟裂的土地上只有枯死的蒿草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
偶尔遇到零星百姓,也都是面黄肌瘦,眼神麻木,如同惊弓之鸟。
他们亲眼见过易子而食后残留的血迹与白骨,亲耳听过失去一切的流民绝望的哀嚎,也遭遇过几波同样活不下去、沦为匪寇的乱民,幸得护卫拼死才得以脱身。
这一路,仿佛是将京城纸醉金迷之下的累累疮疤,血淋淋地撕开,摊在他们眼前。
昔日心中那个“煌煌天朝”的幻象,在这残酷的现实面前,彻底崩塌,碎成了齑粉。
李崇文时常捧着随身携带的、早已被翻烂的圣贤书,对着车窗外荒芜的景象老泪纵横,不知是为这破碎的山河,还是为自己蹉跎半生的信仰。
然而,与这绝望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,是关于北方那个边城的消息。
越是靠近朔州,关于那里的传闻就越是具体、越是真切。
不再是虚无缥缈的“有粥喝”,而是变成了“萧世子亲自抗疫情”、“楚公子妙计安民心”、“流民自愿参军,血战不退大破朝廷军”……这些消息如同黑暗中的火把,不仅照亮了他们前行的道路,更一点点重新点燃了他们早已冰冷的心。
“想不到,这世间……竟还有如此所在。”张士珩望着北方,喃喃自语。
他心中的热血,并未完全冷却,只是被京城的污浊所冻结。
如今,这北境的风雪,似乎正将那冰层吹裂。
当他们的马车终于越过标志着朔州边界的那道已然修复、并有精神抖擞的兵士驻守的关隘时,眼前的景象让他们几乎以为自己踏入了另一个世界。
关隘之内,虽然也能看到战争留下的痕迹,破损的营寨、新立的坟茔,但秩序井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