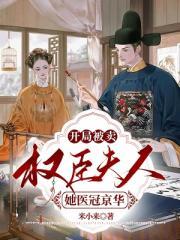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我在现代留过学 > 第一千零七十五章 能背锅就多背锅(第2页)
第一千零七十五章 能背锅就多背锅(第2页)
他的宅邸随后被抄,搜出一本私人日记。最后一页写道:
>“我以为吃人是为了强国,后来才明白,强国只是为了让我继续吃人。我不是为了国家才堕落,我是借国家之名,行兽行。如今铃声日夜响于耳畔,闭眼便是那些孩子站成一排,笑着递给我药丸,说:‘大人,请用,这是我们的命熬的。’”
这本日记被公开刊印,发放全国。许多曾为官者读后彻夜难眠,纷纷主动投案。但也有人冷笑:“疯了,全都疯了!不过是些幻象、谣言,怎能让整个朝廷为之动摇?”
可就在他说完这句话的当晚,他府中的井水变成了墨汁,仆人打捞上来一只腐烂的手,手中紧握一张发黄的纸条,上书:“壬戌年三月十二,你也在这名单上。”
恐惧像瘟疫般蔓延。人们开始互相怀疑:谁是下一个被记忆追上的?谁的心里藏着一口未曾察觉的井?
耶律琚却没有停留。他知道,第十三井虽已开启,但远未干涸。麻木不会一夜消亡,它会变形,会伪装,会躲在“我只是奉命行事”、“我又改变不了什么”、“别人也这样”的借口背后苟延残喘。
他南下福建,重返莆田。
林知远故居早已荒废,院中槐树被雷劈过,半边焦黑。他在屋后掘地三尺,果然挖出一口小井,井壁刻满细小文字,全是当年被焚试卷的残句。最深处,埋着一只陶罐,内藏三百七十一张纸条,每张写着一个名字、籍贯、年龄。其中一张边缘烧焦,勉强可辨:“林知远,二十四岁,死于忠。”
他将陶罐带回,在村口召集乡民。
“你们还记得他吗?”他举起纸条。
众人沉默良久。一位白发老妪颤巍巍上前:“我记得……他是我们村里第一个考上秀才的。那年放榜,全村杀猪庆贺。后来听说他死了,都说他是疯了跳井……没人敢提。”
“因为他说了真话。”耶律琚说,“而你们选择了忘记。”
老妪突然跪下,痛哭失声:“我儿子也是读书人……落第后天天念叨‘官逼民反’,被抓走那天,我还骂他惹祸……三年后才听说,他是被活活打死的……”
话未说完,周围已有数十人相继跪倒。有人忏悔曾为求自保举报邻里私议朝政;有人哭诉女儿因拒绝进“养童坊”被诬通敌;还有人坦承自己吃过“勇武丹”,如今夜夜梦见咬断亲弟喉咙。
耶律琚静静听着,直到最后一人说完,才将陶罐打开,把纸条逐一投入火盆。
火焰腾起,却不灼手,反而散发出淡淡的书香。纸条燃尽之际,空中浮现一行大字,如星辰排列:
>**“记住,就是反抗。”**
翌日清晨,莆田县衙门前多了一块新立的石碑,无名氏所立,仅刻两行字:
>此地曾有一人,因言获罪。
>今日仍有千人,因惧沉默。
此事迅速传开。各地民众纷纷效仿,自发为被抹去的历史立碑。有的立在焚书旧址,有的嵌入废弃贡院墙角,甚至有人将碑文刻在自家灶台、床头、墓碑背面,只为让子孙每日可见。
就连宫中也不得安宁。赵煦某日翻开祖宗实录,发现原本空白的一页竟浮现出墨迹,乃是仁宗晚年亲笔补记:
>“朕执政四十二年,自谓宽厚爱民。然有谏官陈仲淹上书言‘三冗三费’,切中时弊,朕因其言太过激烈,贬其出京。后闻其贫病交加而死,妻儿乞食街头。朕悔之晚矣。故立‘言官司直’,愿后世君臣,宁听逆耳之言,勿蹈覆辙。奈何继者不知珍惜,竟使之湮灭。此乃我宋室之耻,亦朕一人之罪。”
这段文字出现后,皇宫藏书阁所有被删改的史册均自动恢复原貌。太傅们惊恐万分,欲加遮掩,却发现只要有人阅读真相,书页便愈发清晰,直至金粉浮现,宛如天启。
而此时,甘兰进带来最新密报:北方草原部落开始退兵,首领遣使称,“闻南朝鬼神显灵,正气复苏,不敢犯。”南方诸国亦派使者前来朝贺,言“中华重振纲常,实乃天下之幸”。
可耶律琚只是摇头。
“鬼神从不存在,存在的只是人心。”他对崔元朗说,“他们怕的不是亡魂索命,而是活人觉醒。”
![职业反派[快穿]](/img/1085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