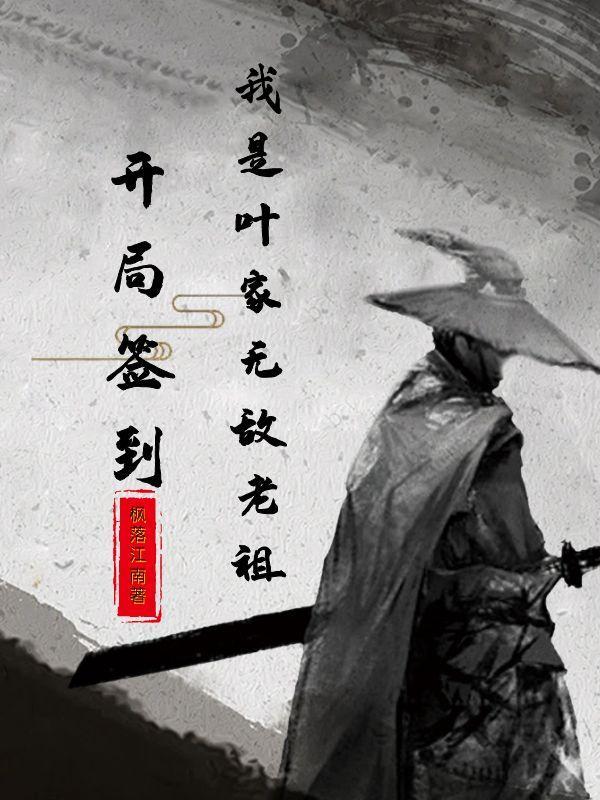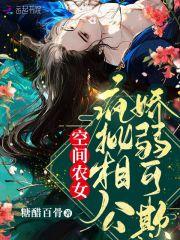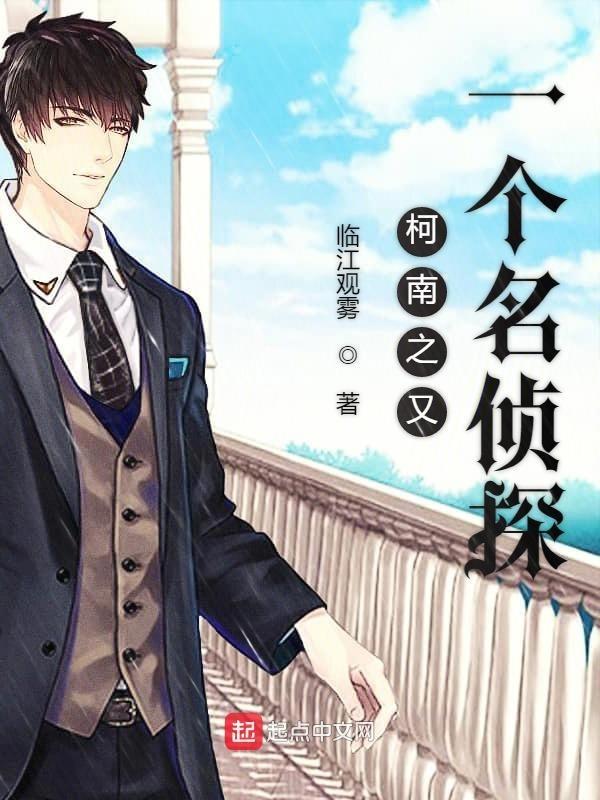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那年花开1981 > 第五百三十九章 连你都看出来了(第1页)
第五百三十九章 连你都看出来了(第1页)
李野参观计算机展会之后的第二天,董善离开了京城,带着一大票人才赶赴了西南。
李野看过最终确定的“支援人员”名单,其中赫然有曾经的老同事岳玲珊和赖佳仪。
岳玲珊是李野刚刚参加工作时候一个办公。。。
晨光未散,雾气还缠在厂房的钢梁之间,李野已经站在了研发大楼顶层的观测廊道上。他手里攥着一份刚打印出来的数据报表,纸页边缘被露水洇湿了一角,但那上面的数字却清晰得刺眼??西南项目第三季利润同比增长百分之五十七,客户满意度评分首次突破九十分大关。这本该是庆功的日子,可他的眉头却越拧越紧。
因为就在昨夜,一封匿名信寄到了一分厂工会办公室,内容只有三行字:“你们改的是制度,动的是饭碗。再往前一步,血要流。”笔迹潦草,墨色深浅不一,像是在极度紧张中写就。马兆先天没亮就找上门来,把信拍在桌上时手还在抖:“这不是吓唬人,这是杀意。”
李野没说话,只是把信折好,放进公文包最底层。他知道,这场仗早已不是理念之争,而是利益切割的刀锋对决。董善虽暂时退却,但他背后那张网还在,根须深埋于体制缝隙之中,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如今西南的成功像一面镜子,照出了太多人的不堪与虚弱,有人坐不住了,自然要出手。
上午九点整,全厂中层干部会议准时召开。会场设在一楼多功能厅,原本能容纳三百人的大厅只坐了不到一半。这不是缺席,而是震慑后的沉默。李野走进去时,不少人低头翻文件,没人敢迎视他的目光。他站上讲台,没有开场寒暄,直接打开投影仪,调出一张组织架构图。
“从今天起,成立‘改革监督委员会’。”他说,“由一线工人代表、技术骨干、财务审计人员和外部法律顾问组成,直接受市经委指导,独立于现有管理层运作。所有涉及外派项目、资金调配、人事任免的重大决策,必须经其审议备案。”
台下顿时炸开了锅。
“这算什么?架空我们?”企管科一个副科长猛地站起来,“厂长您这是不相信自己的班子?”
“我不是不信班子。”李野声音不高,却压住了嘈杂,“我是信不过那些藏在流程背后的手。谁贪过一笔预付款,谁批过一张虚假报销单,心里都清楚。我不点名,不代表我不知道。”
那人脸色煞白,缓缓坐下。
柯老师坐在角落,默默听着,手指轻轻敲击桌面。他知道李野这一招有多险??表面是阳光政务,实则是把权力重新洗牌,将原本属于厂级领导的话语权,部分让渡给基层与第三方。此举一旦推行,不仅动摇既有利益格局,更可能引发上级部门警觉:一个分厂,竟敢自建监督体系?
散会后,柯老师拦住李野:“你这是往雷区里跳。”
“雷早就埋好了。”李野望着窗外正在装卸新零件的叉车,“我只是提前踩一脚,看看哪颗会炸。”
当天下午,市国资委果然来电质询。电话是辛琦接的,他语气平静地解释:“一分厂作为全市国企改革试点单位,有权探索新型治理模式。况且,监督机制并非对抗组织,恰恰是为了更好地执行党的纪律。”挂了电话,他对秘书说:“备车,我要去一趟西南。”
与此同时,陈志明在西南重汽的日子并不好过。尽管职务恢复,文件解封,但他办公室门口每晚都有不明身份的人徘徊,食堂饭菜也屡次被人动过手脚。最严重的一次,他在车间巡查时,头顶的吊装轨道突然松脱,千钧一发之际被一名年轻焊工扑倒,才躲过致命一击。事后查监控,那段录像恰好“故障”。
李野得知后,连夜召集安保团队开会。他不再掩饰愤怒:“从现在起,外派人员实行轮岗制,每两周更换住所;每人配备紧急联络器,二十四小时专人值守;家属信息全部加密管理,严禁泄露。”他又转向马兆先:“联系老张,让他从退休工人里挑二十个信得过的,组成‘护厂志愿队’,待遇按特种岗位发放。”
马兆先迟疑:“这些人年纪都不小了……”
“正因为他们老,才不怕死。”李野冷冷道,“他们经历过饥荒、动荡、下岗潮,知道什么叫真正的苦。现在这点威胁,在他们眼里不过是小儿科。”
三天后,第一批“志愿队员”抵达西南。他们穿着旧式工装,胸前别着褪色的劳动奖章,走路带风,眼神如铁。带队的是老张本人,五十多岁,鬓角全白,腰板挺得笔直。他在欢迎会上只说了一句:“咱们不是来享福的,是来守规矩的。谁想毁这一摊子,先问问我们这些老骨头答不答应。”
当晚,厂区围墙外蹲守的黑影消失了。
然而风暴并未平息。一周后,《奉天日报》刊发一篇题为《警惕“模式输出”背后的隐忧》的评论文章,署名“资深观察员”。文中质疑一分厂借支援之名行扩张之实,涉嫌“变相控制外地企业”,并暗示其管理模式“过于激进,脱离国情”。文章措辞谨慎却暗藏杀机,引来了多家媒体转载。
李野看完报纸,冷笑一声:“终于动手了,舆论战。”
柯老师皱眉:“这篇文章背后有笔杆子,不是普通记者能写的。很可能是市委宣传口的人授意。”
“那就用事实打脸。”李野当即下令:“把西南三个月来的生产数据、员工收入变化、客户反馈整理成白皮书,配上视频资料,发给所有合作单位,同时抄送市纪委、发改委、总工会。”
他还特意加了一句:“标题就叫《劳动者的声音,比任何评论都真实》。”
白皮书发布当天,反响远超预期。三家已签约引进管理模式的车企公开表态支持,称“这才是看得见、摸得着的改革成果”;省总工会转发全文,并附言:“工人增收、企业增效、社会增信,这样的模式为何不能推广?”更有意思的是,一位曾在一分厂工作过的退休工程师在网上发文回忆:“过去我们修一台车要拆三次,现在一次搞定。不是人变了,是制度让人敢负责。”
舆情迅速逆转。原本报道质疑的媒体纷纷删帖或低调回应。那位“资深观察员”再未发声。
但李野清楚,真正的较量仍在暗处。果然,十天后,财务科发现异常??一笔总额八百万元的技术服务费,未经审批便从一分厂账户划出,收款方是一家注册于海南的空壳公司。经查,转账指令系通过内部系统远程操作,IP地址显示来自市机械局某下属单位。
“这是栽赃。”马兆先咬牙切齿,“他们想让我们背黑锅!”
李野却异常冷静:“不急。让他们走完流程,等钱到账再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