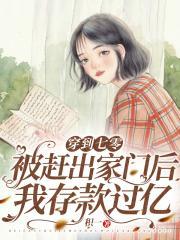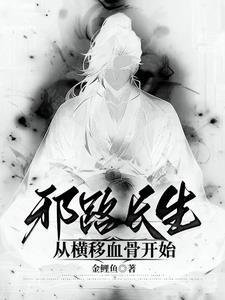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乌龙山修行笔记 > 第五百五十八章 逃离(第2页)
第五百五十八章 逃离(第2页)
“这是我当年的工作日志。”他说,“每一条删除指令,每一个被销毁的档案编号,每一桩被迫沉默的案件……我都记下了。我知道这些本该烧掉,可我烧不了。夜里一闭眼,全是哭声。”
韩念接过本子,翻开一页,只见某行写着:“1976年4月5日,天安门前群众悼念活动,定性为反革命事件。建议全面清除相关影像资料及口述记录。执行人:林修远。”
再翻一页:“1989年6月,南方某高校学生组织读书会,讨论宪政民主。参与者共三十七人,均已控制。其中十二人思想顽固,建议长期监控。备注:有一人年仅十六岁,系烈士子女。”
韩念合上本子,深吸一口气。
“你不怕公布这些,会引发动荡?”
“怕。”林修远坦然道,“但我更怕继续骗自己。这些年,我梦见过太多孩子的眼睛。他们不该被当成敌人。”
韩念转身走进塔内,片刻后捧出一支玉骨笔??通体幽蓝,笔杆上缠绕着细小的蓝花纹路。
“这支笔,曾属于一个被你下令开除的大学教授。”韩念将笔递给他,“他死前最后一句话是:‘历史不会原谅篡改者,但或许会宽恕悔悟者。’”
林修远双手颤抖接过,仿佛捧着一块烧红的铁。
“我想学怎么写。”他说,“哪怕只剩最后几年,我也想替那些不能说话的人,留下点什么。”
韩念点点头:“那就从第一个名字开始吧。”
当夜,赎忆塔第九层灯火未熄。林修远伏案疾书,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清晰可闻。沈清梧守在一旁,偶尔为他添茶。阿舟则坐在角落,始终未发一言,但也没有离开。
直到凌晨三点,林修远写下最后一个名字,忽然身体一晃,咳出一口血。
“别硬撑。”沈清梧扶住他,“你可以明天继续。”
“不。”他摇头,“有些事,晚一天都是罪过。”
他指着稿纸上的最后一行:“这个女孩,叫周晓芸,二十一岁,物理系学生。她在一次秘密会议上提出‘言论自由应受宪法保护’,被举报后关押半年,精神失常,出院当晚跳江自杀。她的父母至今不知道女儿为何而死。”
“我要让世人知道。”他说,“她是为理想而死的英雄。”
沈清梧看着那行字,眼眶微红。她想起自己父亲被捕那天,也是这样年轻的面孔,也是这样坚定的眼神。
第二天清晨,这篇《忏悔录?第一辑》被录入《人间录》,并通过全球承忆网络同步发布。短短六小时内,点击量突破千万。评论区没有谩骂,只有无数人留言:
“晓芸,我们记住你了。”
“爸爸,原来你也曾为正义发声。”
“谢谢你敢写下来。”
与此同时,全国各地掀起新一轮“记忆归档”热潮。图书馆地下库房陆续开放尘封档案;民间自发成立“寻名小组”,奔赴偏远山村寻找幸存证人;更有年轻人组建骑行队,沿着当年知青下乡路线,逐村采访老人。
而在西北某小镇,一位八十多岁的退休教师在电视上看到林修远的影像后,当场昏厥。醒来后,他拉着孙子的手说:“去把我床底那只铁盒拿来。”
盒中是一叠手抄笔记,记录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本地被打成“右派”的一百四十三人名单,以及他们各自的结局:劳改、自杀、病死、失踪……
“这些人,不该是历史的空白。”老人泣不成声,“我藏了六十年,现在,该还给他们一个名字了。”
这份名单被命名为《沉默者名录》,成为《人间录?共生卷》增补篇的第一份正式材料。
然而,并非所有人都选择面对。
某省委大院内,一名高级官员看完新闻后怒摔茶杯:“荒唐!让一个叛徒写忏悔书,还全国传播?这是动摇国本!”
他当即召集心腹密议,拟了一份《关于遏制赎忆塔非法活动的紧急建议》,主张以“危害国家安全”罪名查封乌龙山,逮捕韩念等人。
消息传出,海外承忆使团集体发声抗议。艾米丽?陈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言:“一个民族的伟大,不在于它从未犯错,而在于它敢于直面错误。中国正在经历一场静默的觉醒,你们要阻止的,不是一个组织,而是一个民族的灵魂自救。”
与此同时,俄罗斯、德国、南非等国的历史学者联名致信中国政府,称愿派遣专家协助建立国家级记忆档案馆,确保这段转型期的历史得以完整保存。
舆论压力之下,那份镇压提案最终未能通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