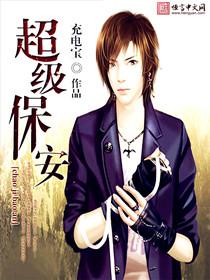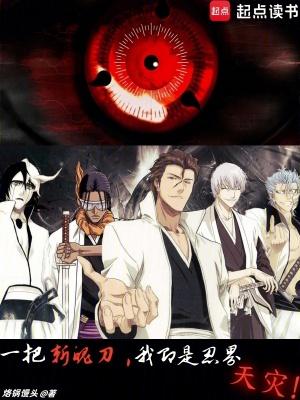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完蛋,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> 第905章五虎闹长安(第3页)
第905章五虎闹长安(第3页)
>吾死之后,勿葬,勿祭,勿谥。
>将吾骨灰撒于黄河源头,随水流遍九州,赎我三十年昏聩之罪。”
全书最后一页,附有一封刘仁的公开信:
>“我们总以为真相是一把钥匙,能打开所有锁链。
>可有时,真相本身也是一道锁。
>它让我们看清黑暗,却未必能带来光明。
>但我依然选择揭开它。
>因为只有当人们有权知道全部事实,包括那些令人痛苦、动摇信念的事实,自由才真正存在。
>历史不该是安慰剂,而应是手术刀。
>即使割开的是我们共同的伤口。”
此书一出,天下震动。
长安街头巷尾议论纷纷。有人痛哭先帝悲惨境遇,有人怒斥太后虚伪奸诈,更多人开始反思:如果连“皇帝是否死亡”都可以被集体隐瞒三十年,那么我们所相信的其他一切,又有多少是真实的?
民间掀起“自省潮”。各地百姓自发组织“证言会”,讲述家族隐藏多年的往事:某村曾集体作伪证陷害清官;某世家祖传田契实为强占所得;甚至连一些寺庙都被揭发伪造灵异事件骗取香火……
与此同时,朝廷陷入空前危机。李显虽力主改革,但面对如此庞大的信任崩塌,亦束手无策。最终,他下诏宣布:
**即日起,废除“钦定正史”制度,设立“万民修史台”,凡年满十六者皆可提交见证材料,经核实后录入国家档案,永久公开。**
十年后,一座巨大的石碑林在洛阳郊外建成。碑上刻满密密麻麻的文字??不是帝王功绩,而是普通人写下的真实经历:
“我曾在饥荒年吃人肉。”
“我举报邻居藏书,换来三斗米。”
“我父亲是北苑刽子手,一生杀三百余人。”
“我母亲为保全家,亲手溺死新生女婴。”
而在中央最高处,立着一块无字碑。
据说,那是留给未来的。
又三十年,刘仁的名字再次浮现。
一位西域学者著书《东方醒世录》,称其为“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自觉消解作者权威的思想者”。而在南方小镇,孩子们仍在春分日朗读《凤鸣录》。只是如今版本太多,已分不清哪一句出自最初的手稿,哪一句来自某个农夫的回忆。
某个黄昏,一位旅人路过传书堂,见一位白发老人正在教孙子写字。
纸上写着:
“执笔者众,存心者恒。”
旅人问道:“这本书,到底是谁写的?”
老人笑了笑,指着远处田野里劳作的人群:“你说呢?每一个愿意记住真相的人,不都是作者吗?”
雨又下了起来。
风穿过屋檐,吹动檐下铜铃,叮咚作响。
仿佛在回应某种永恒的追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