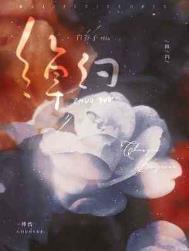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完蛋,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> 第906章没有一个好人(第1页)
第906章没有一个好人(第1页)
五更三点,晨钟击破长安的黎明,百官循着熹微晨光,自朱雀门鱼贯而入。太极殿内,鎏金铜柱映着初升朝阳,流光隐现。
李治立于丹墀之下,一身太子装束,衬得他身姿愈发挺拔帅气。此刻他手中并无奏板,只捧着数。。。
雨声渐密,檐下铜铃摇荡,那叮咚之声仿佛自三十年前的春分夜延续至今,未曾断绝。传书堂内烛火微晃,老人搁下笔,墨迹未干的宣纸上,“执笔者众,存心者恒”八字静静躺着,像一句誓言,也像一场漫长的回音。
孙子仰头问:“爷爷,为什么我们要写这些?没人会记得吧。”
老人不答,只将纸轻轻吹干,放入一只桐木匣中。那匣子已有些年头,边角包铜泛绿,锁扣上刻着半枚残印??“凤鸣令”三字依稀可辨。他起身走到香案前,打开匣盖,取出一叠泛黄的手稿,最上面那页写着《地宫遗言》四个小楷,字是刘仁誊抄的,笔锋里藏着颤抖。
“有人会记得。”老人说,“只要还有人愿意读,就有人记得。”
话音刚落,院门忽被推开,一道身影踉跄而入。来人披着蓑衣,浑身湿透,怀里抱着个油布包裹,模样狼狈,却眼神坚定。他跪倒在门槛处,喘息道:“我……从洛阳来。碑林那边……出事了。”
屋内众人皆惊。孙七娘虽已八十高龄,仍拄拐起身,声音如铁:“说。”
那人抹去脸上雨水,颤声道:“昨夜雷暴,一道闪电劈中无字碑……碑面裂开一道缝,里面……藏着东西。”
“什么?”
“一块玉符,还有一卷竹简。竹简上有字,是用朱砂写的,只有八个字??**‘真死非亡,假活即囚’**。”
满堂寂静。
刘仁若在,定会认出这八字出自他最初废弃的草稿页。那是他在键盘前熬夜时随手敲下的设定碎片:他曾设想先帝并未真正活着,而是太后以秘术操控其躯壳,借“活尸”之名维持摄政合法性。后来觉得太过荒诞,便删去了。可如今,这句话竟从地底浮现,像是某种宿命的补遗。
老人缓缓坐下,手指抚过那八个字的摹本,良久才道:“这不是刘仁写的。”
“那是谁?”孙子怯怯地问。
“是真相自己写的。”老人低语,“当谎言埋得太深,真相就会自己长出来,哪怕借一副早已死去的笔骨。”
翌日清晨,一支由老少僧俗组成的队伍启程前往洛阳。他们没有旗帜,没有号令,只是默默前行。沿途百姓见之,自发焚香让道,孩童捧书相送。有人认出其中一名盲人手持三弦琴,正是当年《唤魂调》的传人;另一名老妇肩胛处隐约可见箭疤,走路微跛,却是孙七娘亲随。
七日后,他们抵达碑林。
无字碑果然裂开,裂缝如蛛网蔓延,中央嵌着一块青玉符,形似龙首,背面阴刻“承命非承位”五字??与刘仁当年所持青铜牌竟为一对。考古匠人小心取出竹简,发现其材质非竹非木,乃是取自太庙地宫深处的“冥简”,以特殊药水浸泡千年不腐。展开后,全文共三百二十七字,署名赫然是:
**“大周孝昭皇帝口述,宦官张守义笔录”**
内容如下:
>“朕确未死,然亦非生。
>太后初时奉群臣密议,以秘法续朕性命,实为护国。然十年之后,权柄尽归其手,朕成傀儡。彼时欲醒不能,欲言不得,唯余指尖可动。每至朔望,她亲来喂药,笑曰:‘陛下安好,天下太平。’
>吾恨不能怒,不能哭,只能任岁月蚀骨。
>直到某夜,一盲眼乐工潜入地宫,以鼓槌叩壁三长两短。朕知那是太子旧约,遂竭力回应。此后三年,此人每夜来叩,吾以指划床板记事,托其带出。然终事发,彼被沉洛水。
>朕自此绝望,唯愿速死。然太后令人剜去朕舌根,断声带,防吐露只言片语。
>她说:‘你要活着,做我的镜子,照见权力如何不动声色地杀人。’
>死亡易,沉默难。
>今碑裂天现,或为报应。
>我留此符,非求昭雪,只为警示:
>当一个人可以被剥夺言语、记忆、死亡的权利时,
>体制即为刑具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