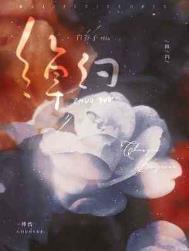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完蛋,我来到自己写的垃圾书里了 > 第906章没有一个好人(第2页)
第906章没有一个好人(第2页)
>安宁即是暴政。
>愿后人勿以‘稳定’之名,行禁声之实。”
全文读罢,全场肃立。
盲人琴师忽然盘膝而坐,拨动琴弦。第一个音落下时,风停了。第二个音起,乌云散开一线。待整段《唤魂调》奏毕,阳光破云而出,正照在那裂开的无字碑上,仿佛天地也为之动容。
就在此时,远处尘土飞扬,一队骑马之人疾驰而来。为首者身着青袍,胸前绣有“万民修史台”字样,下马拱手道:“诸位前辈,京中急讯??国子监祭酒昨夜自缢于藏书阁,遗书仅一句:‘我配不上那把钥匙。’”
众人默然。
赵十三之孙??如今已是火器坊主??冷笑一声:“他早该死了。三十年前是他亲自将药汤送入地宫,一碗一碗,喂给一个清醒却不能说话的皇帝。他不是不知情,他是共犯。”
“可他也守护了秘密。”盲人琴师轻声道,“直到最后一刻才崩溃。这种人……比纯粹的恶更可怕。他们是沉默的帮凶。”
老人点头:“所以更要让他的名字刻上碑林。”
“什么?”有人惊问,“为自杀者立碑?”
“不。”老人目光如炬,“要刻下他一生经手的三百七十二份篡改史册名单,连同他父亲、祖父所为。让后人知道,谎言是如何一代代传承的。”
数日后,新一批石碑竖立。其中一块赫然写着:
>**“李氏三代修史官,共删改《实录》一百零三次,掩盖饥荒六次、冤狱十九起、皇室丑闻七件。末代祭酒李文渊,知而不止,终自尽。罪不在死,在生时之不作为。”**
与此同时,长安城内掀起新一轮风暴。民间自发组织“清源会”,专事挖掘家族黑历史。有士族子弟公开祖宗贪污证据,自愿退还田产;有老尼姑揭发寺院私藏军械,曾助叛军围城;甚至皇宫旧宦后裔站出来承认,先辈曾在御膳中下毒,只为换取升迁。
李显皇帝面对滔天舆情,闭宫三日。第四日清晨,他亲赴碑林,在无字碑前焚香跪拜,然后当众宣布:
**“自今日起,每年春分定为‘省罪日’。凡官员就职、学子科举、将士受勋,皆须至此诵读碑文一日,而后方可履职。另设‘逆耳司’,专收百姓对朝廷的控诉文书,无论言辞激烈与否,不得追责,且必须逐条回复。”**
诏书下达当日,万里晴空突降暴雨。人们说,那是先帝在哭。
而在这场风暴中心,那个曾化名为“苦觉”的刘仁,早已不知所踪。
有人说他隐居西域,在敦煌莫高窟抄经度日;有人说他东渡扶桑,将《凤鸣录》译成异国文字;还有人说他在终南山深处结庐而居,每日书写一部新史,写完便投入炉中焚毁,灰烬随风撒向黄河上游。
但小镇上的孩子们坚信他还活着。
每逢春分,他们会在传书堂外摆放一碗清水、一支竹笔、一张白纸。据说,清晨推门时,常发现纸上多了几行字迹,墨色淡如烟痕,内容却是当下未解的谜题:
>“谁下令烧毁北境边防图?”
>“为何净慧庵地窖藏有三百具童尸?”
>“国库历年亏空,究竟流向何处?”
这些问题没有答案,却成了新一代少年的功课。他们组成了“寻真社”,走村串镇,访老问故,将口述记录整理成册,命名为《未竟录》。
十年过去,《未竟录》已有三百卷,藏于传书堂地下密室。每一卷开头都写着同一句话:
**“本书由无数普通人共同撰写,作者无名,但心不死。”**
又一个春分夜,风雨如旧。
一位少女独自来到碑林,在无字碑前点燃三支香。她是陈望的曾孙女,职业是“记忆修复师”??专门帮助因战乱失忆的老人找回过往。她从怀中取出一枚铜铃,轻轻摇响。
叮??咚??
铃声清越,穿透雨幕。
忽然,一阵风吹过,带来远处隐约的琴音。她循声而去,在树林深处看见一位白发老者独坐石上,正在弹奏《唤魂调》。琴声苍凉,仿佛从地底传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