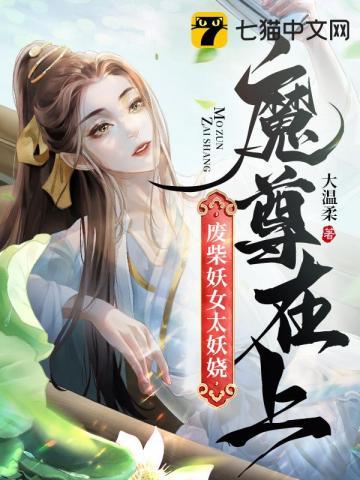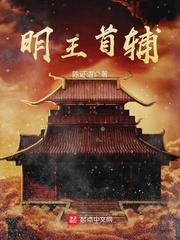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人间有剑 > 第两百二十七章 我有些朋友(第1页)
第两百二十七章 我有些朋友(第1页)
几人在顷刻间加入战场,一时间,这座庭院里,光华璀璨,俨然让没有见过大世面的两个少年都愣住了。
孙亭倒是反应足够快,很快就拍了一把吕岭,这个时候,失神分心,不是什么好事。
吕岭合上嘴,开始担忧起来,“孙哥,老关那家伙,不会出事吧?”
这会儿他都看不清楚那边庭院里的景象了。
孙亭想要下意识摇头,但想了想之后,还是说了句比较稳妥的话,“看样子还行,关先生不是一般修士。”
这话的确也是废话了,什么一般修士能。。。。。。
雪融成溪,顺着莲林小径蜿蜒而下,汇入山脚那口古井。井水清澈见底,倒映着天光云影,也映出谢无尘的身影??他坐在梅树下,膝上铜铃静默,手中却多了一支笔,一支用铃兰花茎削成的细笔,尖端微弯,似钩似铃舌。
少年站在三步之外,不敢近前。他叫阿石,南疆人,母亲是村中织女,父亲早年死于战乱。她临终前将这本《心语录》残卷交给他,说:“你若迷了路,就去找谢无尘。他会告诉你,人心不是石头。”
谢无尘没再说话,只是蘸了井水,在石桌上写字。水痕清晰,字迹如刻:
**“善念如灯,不怕风大,只怕无人添油。”**
阿石看得懂,却不懂为何要写在石头上。他想问,又怕惊扰这份沉静。
忽然,井中涟漪轻荡,水面文字竟缓缓游动,化作一行行细小蝌蚪,顺溪流而去。它们穿过碎铃小径,越过荒草坡,一路向东,最终渗入地下暗河,流向四面八方。
与此同时,东海归心书院的少女正伏案抄录新得的信文。忽觉砚台震动,墨汁自行爬升,在纸上勾勒出陌生字句。她惊起,只见纸上浮现的正是谢无尘所写的那句话。她怔住,随即展颜一笑,提笔续道:
**“我愿做那添油的人,哪怕只照亮一寸夜路。”**
墨迹未干,窗外风雨骤至。一道闪电劈落,击中书院后山古槐。槐树焦裂,却从中滚出一只陶罐,罐口封泥印着“无声铃舍”四字。少女冒雨拾回,启封一看,竟是七十三枚孩童乳牙,每一枚都系着红绳,背面刻有名字。
她颤抖着翻找,终于在最后一枚上看见自己的姓氏。
“原来……我也曾是那里的一员。”她喃喃。
而在江南祠堂,史官背着箱子踏上第一处乱葬岗。春雨淅沥,泥土松软,他跪在坟前,亲手挖开一座无名墓穴。棺木腐朽,只剩半截骨架与一枚铜铃。他轻轻拾起,拂去泥尘,铃身裂纹中竟渗出淡淡金光。
“你是第七十二个孩子。”他低声说,“我来接你回家。”
话音落时,远处传来脚步声。一位老农撑伞而来,怀里抱着一块破布裹着的东西。“这是我犁地时翻出来的。”他说,“看着像个人形,我就带回来了。”
史官解开布包,赫然是一具干枯的童尸,蜷缩如初生婴儿,双手紧抱胸口。他小心翼翼掰开手指,里面藏着一片纸屑,上面写着三个字:
**“我想娘。”**
史官痛哭失声。他知道,这是最后一个没能逃出火场的孩子。他脱下外袍,将尸身裹好,郑重放入随行木箱。“等所有名字都刻进新祠,”他说,“我会为你点七十二盏长明灯。”
南疆山谷,独臂女子正在教几个孤儿写字。她们围坐在院中石桌旁,用炭条在青石板上练习。一个女孩写得很慢,一笔一划都带着颤抖。她忽然抬头:“姑姑,为什么我们要学写字?村里人都说,认字没用。”
女子不答,只从袖中取出那本《心语录》,翻开一页递给她。上面是阿禾的手迹:
>“字是心的声音。你不说话,它替你说。”
女孩低头看,眼泪砸在石板上。她忽然用力写下两个歪斜的大字:“我想活。”
众人皆静。连檐角铜铃也停了片刻。
良久,女子抬起左手,虚影之手轻轻抚过她的发丝。那一瞬,整座院子仿佛被暖光笼罩。断翅的鸟再次飞来,绕屋三圈,落在小女孩肩头。
“它记得你。”女子微笑,“所以它回来了。”
西域望灯镇,第九十九盏灯已燃尽。驼童点燃第一百盏时,手有些抖。小女孩捧着红灯笼站在“心”字中央,忽然说:“叔叔,今天有人哭了。”
驼童一愣,顺着她目光望去,只见镇口站着一对夫妇,女人怀里抱着襁褓,男人蹲在地上,掩面而泣。
“我们丢了孩子九年。”男人哽咽,“昨夜梦见她回来,说‘爹娘,我在有灯的地方’。我们就一路寻着灯火走,走到这里……再也走不动了。”
驼童默默牵起小女孩的手,将她带到这对夫妇面前。
“看看她。”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