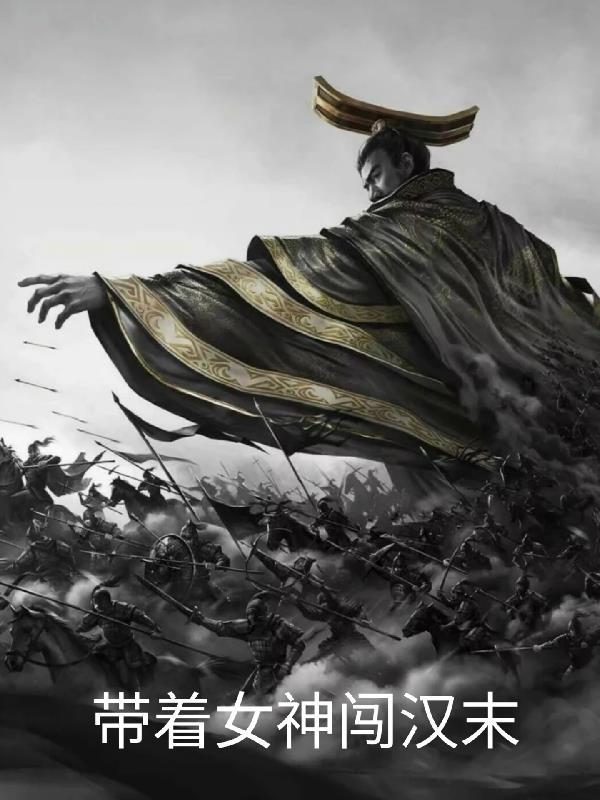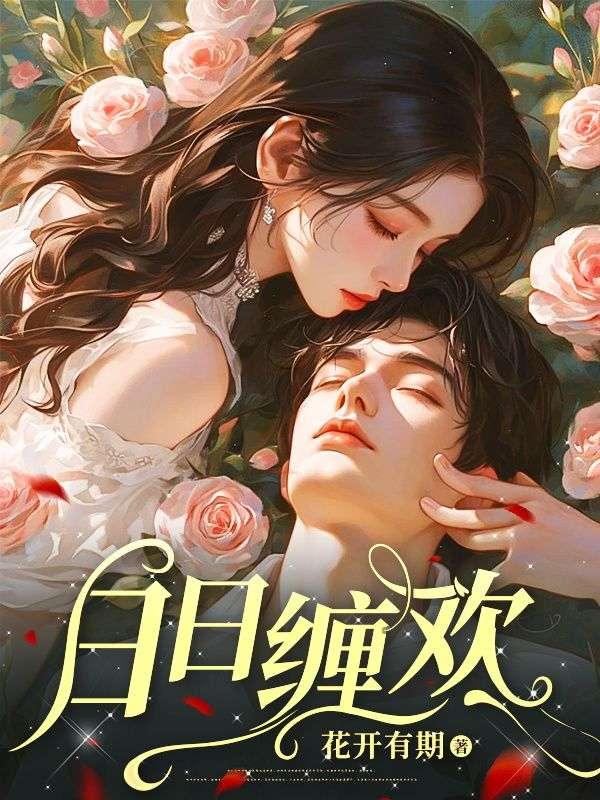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重启人生 > 0490电脑硬件杀手和解谜游戏(第3页)
0490电脑硬件杀手和解谜游戏(第3页)
一周后,晓宇主动提出要回老家一趟。
“我想看看奶奶。”她说,“还想见见村口小学的孩子们。他们给我写了信,说想听我讲诗。”
许风吟没有阻拦。他联系了当地妇联和心理辅导团队,安排全程陪同。临行前夜,他把那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送给她。
“带着吧,”他说,“它陪过很多人走出黑暗。”
她接过书,抚摸着封面磨损的边角,轻声问:“你会一起去吗?”
他摇头:“这次你要自己走。我只是在终点等你。”
车子驶离城市的那天早晨,天空澄澈如洗。晓宇背着旧书包,里面除了课本和蜡笔,还有三十二张录好声音的U盘??是小满班上的同学们让她转交的“回音”。
抵达村庄时已是午后。老屋门前槐花开得正盛,香气扑鼻。奶奶拄着拐杖站在门口,眼眶通红。她一把抱住晓宇,嘴里喃喃:“丫头,你回来了……你真是我的丫头啊……”
村里人陆续围过来,有好奇的,有唏嘘的,也有躲闪目光的。伯父被带走调查的消息早已传开,有人说他罪有应得,也有人嘀咕“亲侄女告发长辈,太狠心”。
晓宇没理会那些议论。她拉着奶奶的手走进屋里,发现墙上贴满了她小时候的奖状??原来老人一直留着。
下午,她来到村小。三十多个孩子挤在教室里,眼睛亮晶晶地看着她。校长请她讲讲“外面的世界”。
她摇摇头:“我想先给你们读一首诗。”
她翻开那本《现代汉语词典》,找到顾城的《小巷》,一字一句地念:
>“小巷又弯又长我用一把钥匙敲着厚厚的墙……”
读完,她问:“你们有没有试过,对着墙说话?”
一个小女孩举手:“我说过。我家爸妈打架,我就躲进衣柜,对着木板说‘我不想听’。”
另一个男孩低头说:“我梦见我爸打我,醒来发现枕头湿了。我没敢告诉我哥。”
晓宇静静听着,然后从包里拿出U盘,插进教室老旧的录音机。
按下播放键。
瞬间,教室响起一阵阵稚嫩的声音:
>“晓宇姐姐,我喜欢你写的字!”
>“你可以做我的笔友吗?”
>“你不孤单。”
>“我也挨打,但我现在不怕了。”
孩子们听得睁大眼睛,有的悄悄抹泪,有的互相握住手。
放完最后一段,晓宇说:“现在,轮到你们了。每个人都可以写一句话,放进我的书包。我会带回北京,让别的孩子也听见你们的声音。”
纸条很快收上来。她一张张看过去:
>“我想妈妈回来。”
>“我讨厌酒味。”
>“我考了第一名,可爸爸说女孩子读书没用。”
>“我每天都在等一个人对我说‘你很棒’。”
她把这些纸条小心收好,放进贴胸的口袋。
回程路上,她靠在车窗边,看着夕阳下的田野。风吹进来,带着泥土与麦穗的气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