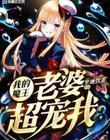书迷阁>重启人生 > 0492进击的游科(第2页)
0492进击的游科(第2页)
田小满伸手抚过信箱上的刻字:“**秘密信箱,永不泄露**”。她低声念了一遍,像是在确认某种誓言。
傍晚,许风吟回到办公室,发现桌上放着一份快递签收单??贵州毕节图书馆签收了那份“特别礼包”。附言栏里,管理员手写了一句:“她来取了,看了很久,抱着书不肯松手。”
他打开电脑,调出“小钥匙”的档案。这个ID来自河北某县城中学,过去三个月共提交七封信,内容从最初的“我爸打我”逐渐变为“今天老师表扬我了”“我交到一个朋友”“我梦见自己站在舞台上唱歌”。最新的留言“今天,我把钥匙插进了锁孔”,系统自动标记为“积极转折信号”。
他点击回复:
>“钥匙转动的那一刻,门不一定立刻打开。
>但黑暗中,你已为自己点亮了一盏灯。
>继续转动它,直到光涌进来。
>我们在这里,等你走出来。”
刚发送,林晚发来消息:“《墙后》播放量破千万了。教育部说,要在全国中小学心理课上放映。还有三十多家媒体想采访你。”
他回:“拒绝所有个人专访。把镜头留给志愿者、老师、孩子。这不是我的故事,是他们的。”
林晚秒回:“明白。我已经剪了一版群像版预告,全是匿名声音配动画。你看下。”
他点开视频。第一个声音是个男孩:“我偷看爸爸的药瓶,上面写着‘抑郁症’。原来大人也会疼。”第二个是女孩:“我妈说我像负担,可我在日记里写,我是自己的光。”第三个是老人:“老伴走了五年,我第一次跟人说起她爱喝豆浆。”……
每一句话落下,墙上便裂开一道缝,透出暖光。
他看完,眼眶发热,回复:“就用这个。”
深夜,他再次翻开自己的词典,在“信”字页新增一行字:
>“我们无法阻止风暴来临,
>但可以建一座屋檐,
>让无处可逃的人,
>至少能听见雨声之外的声音。”
凌晨,系统弹出一条紧急警报:内蒙古赤峰的初三男生连续三天未登录“回音行动”平台,学校反馈其已两天未到校,家访发现家中无人,父亲酒后失联。
许风吟立刻联系当地社工机构,调出该生近期信件记录。最后一封写于四天前:
>“我梦见井底有光。我爬上去,发现是一本书在发光。书上写着我的名字。
>可醒来,我爸又踹了我一脚,说‘废物别装睡’。
>我不想回去了。”
他立即发起“橙色响应”预案,协调警方介入寻人,同时指派两名志愿者驱车前往赤峰,携带心理干预包与应急资金,准备临时安置。
他在工作日志写下:
>“当孩子开始梦见光,说明黑暗已压到极限。
>此刻的每一分钟,都可能是生死之差。
>我们必须比绝望跑得更快。”
清晨六点,好消息传来:男孩在火车站被民警发现,正准备扒火车南下。他身上只有二十块钱,背包里塞着几本练习册和一张“声音邮局”的回信复印件。经心理疏导,他同意暂住学校庇护宿舍,并接受长期跟踪辅导。
许风吟长舒一口气,拨通男孩的辅导老师电话:“告诉他,那本发光的书,是我们正在为他写的未来。他不必逃,我们可以一起改写结局。”
七点,晓宇发来语音:“奶奶今天问,能不能把她的药盒捐出来?她说,那么多孩子睡不着、吃不下、心跳快,也许我们的药,能变成他们的安心丸。”
他笑着回:“告诉她,最珍贵的不是药,是她愿意分享的心意。我们可以做个‘安心盒子’,收集老人们不用的空药瓶,贴上鼓励的话,送给焦虑的孩子。让他们知道,痛苦可以传递,但治愈也可以。”
八点,田小满发来消息:“我昨晚没睡,写了一份教案。第一课,叫‘写一封不怕丢的信’。我想让孩子们知道,信丢了没关系,因为写下的那一刻,心就已经被听见了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