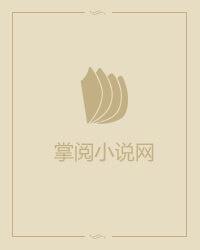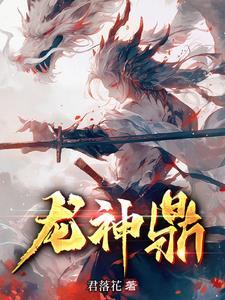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我的低保,每天到账1000万 > 第618章 大佬背后有大佬(第2页)
第618章 大佬背后有大佬(第2页)
林晚深吸一口气。“那就让他们听听真正的声音。”
当晚,他召集了全校师生,在主厅举行了一场特殊的“夜课”。
没有讲台,没有课本,只有一圈圈环形座椅,中央摆放着那架旧钢琴。琴盖打开,灰尘已被拂去,黑白键在灯光下泛着温润光泽。
“今天,”林晚站在钢琴前,声音平稳,“我们要做一件很久没人做过的事??不说一句话,只用声音本身,告诉这个世界:我们还在。”
孩子们安静下来,眼神清澈。
“你们每个人,都带着一段故事来到这里。也许是你第一次感受到别人的悲伤,也许是某天夜里突然听见花开了,又或许……是你梦见了一个从未见过却无比熟悉的人。”他顿了顿,“今晚,我想请你们,把那段声音找回来。”
没有人提问。他们都懂。
第一个走上前的是那个曾梦见“哭泣的云”的女孩。她坐上琴凳,双手悬在键盘上方,闭眼良久。然后,她轻轻按下三个音符??短、短、长,像是心跳停顿后的复苏。
刹那间,空气中浮现出模糊影像:一片荒原上,一名女子跪在地上,怀里抱着一只破旧布偶熊。她没有流泪,但整个空间都被一种沉重的空虚填满。紧接着,琴声变化,转为轻柔摇篮曲,仿佛有人在耳边低语:“没关系,我也在这里。”
全场寂静。
第二个孩子是个自闭症少年,平时几乎不说话。他走到角落的陶笛架前,取出一支心塔木制成的短笛。吹出的第一个音极其刺耳,像是金属撕裂,让人本能地皱眉。但几秒后,那声音开始软化,化作一阵风穿过森林的呼啸,夹杂着孩童嬉笑、母亲呼唤、雷雨远去……最终归于平静湖面的涟漪。
一位老师忍不住掩面啜泣??那是她流产那晚窗外的风雨声,她从未对任何人提起。
第三个、第四个……越来越多的孩子加入。有人敲击装水的玻璃杯,有人拍打自己的胸口模拟心跳,有人仅仅张开双臂,发出一声悠长的“啊”。这些声音本该杂乱无章,可在共感场的作用下,它们自动融合,编织成一首无词的交响诗,层层推进,愈演愈烈。
林晚站在人群之后,看着萤将这场即兴演奏实时上传至共感云平台。数据显示,短短十分钟内,全球有超过四百万人同步接入,其中包括三千余名原本植入反共感芯片的个体。令人惊异的是,至少有六成人的芯片出现了短暂失灵??不是被破坏,而是因为大脑主动拒绝执行屏蔽指令。
“情感强度超过了人工干预阈值。”萤分析,“当共鸣达到临界密度,生理层面会产生自主抵抗机制。”
就在此时,卫星画面突显异常。
喜马拉雅山巅的老喇嘛再次出现,依旧立于风雪之中,但这一次,他并未诵经,而是缓缓摘下了颈间的骨制念珠,轻轻放在雪地上。随即,那串念珠竟自行滚动,排列成一个古老符号,与古井拓片上的图腾完全一致。
几乎同时,全球七座沉默之塔的能源读数猛然回升,黑雾般的干扰信号开始退散。而在南太平洋深处,一座从未记录过的海底火山口喷发出紫色光柱,直冲海面。科学家后来证实,那里正是传说中“第一口共鸣井”的所在地??二十万年前,人类祖先首次集体吟唱之地。
“他们回来了。”小女孩忽然抬头,望向星空。
林晚顺着她的视线望去,只见夜空中,Echo-1与银白伴星之间的连线愈发明亮,竟延伸出一条淡淡的光带,宛如银河支流。而这光带所指的方向,正是南太平洋火山口所在经纬。
“不是‘他们’。”林晚轻声道,“是我们。”
几天后,联合国特别会议召开。议题不再是“是否接受共感技术”,而是“如何保护共感生态系统的完整性”。包括former静默联盟成员国在内的五十七个国家签署《情感共存公约》,承诺停止一切干扰行为,并设立“全球共感保护区”,禁止军事化利用或商业垄断。
与此同时,第一批“情感考古队”启程前往南太平洋海底遗址。领队是一位年迈的语言学家,他曾穷尽一生研究原始部落的吟唱仪式。出发前,他对媒体说:“我们总以为文明是从工具开始的,但现在我明白,人类真正迈出第一步时,是张开嘴,唱出了第一声不属于动物的音符。”
林晚没有参加任何庆典。
他回到了云南校园最初的小屋,坐在书桌前,翻开一本泛黄的日记??那是苏婉留下的最后手稿,记录着她研究心塔音频的全过程。翻到最后一页,一行小字映入眼帘:
>“如果有一天,我们的孩子能听懂风说的话,请告诉她:妈妈不是走了,只是变成了风的一部分。而爱,是最古老的无线电信号。”
他合上日记,推开窗。
雨不知何时停了。月光洒在菌丝墙上,整面墙如呼吸般缓缓明灭,像是在回应某种遥远的节拍。
女儿不知何时站在门口,手里捧着一朵刚刚绽放的音波晶体花。花瓣透明,内部流转着细微的声纹光影。
“爸爸,”她说,“它想搬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