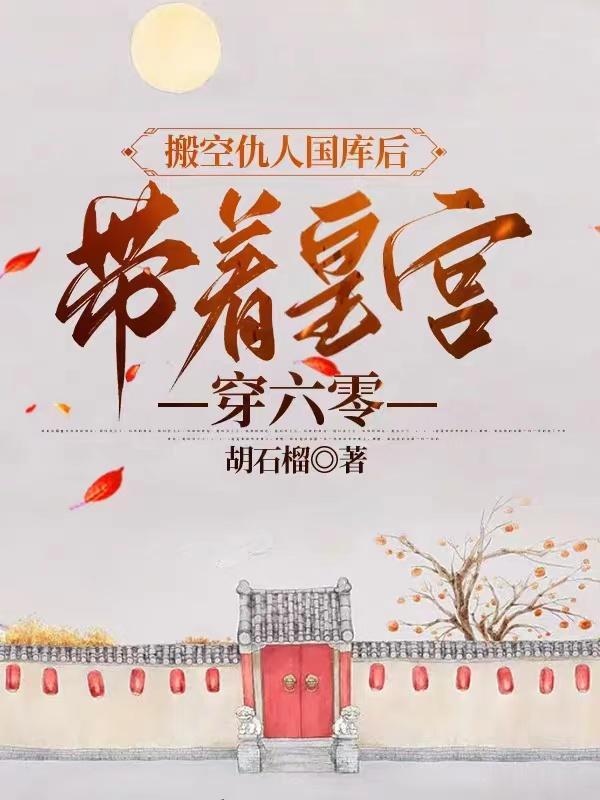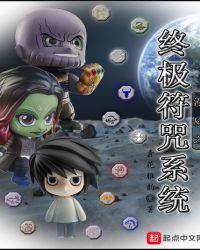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和闺蜜嫁进侯府吃瓜看戏(穿书) > 172第 172 章(第2页)
172第 172 章(第2页)
此事震动朝野。越来越多的地方女官开始挺身而出。湖南有女推官断案时直言:“夫死妻继,古已有之,何须男子批准?”江西一名寡妇率众修渠,立碑铭曰:“此水不归某姓,只润我女儿田。”就连一向保守的岭南士族,也开始悄悄送女儿入学,唯恐将来家业无人承继。
燕宜一路前行,所到之处皆掀起变革波澜。她在岳州设立“女子水利司”,专管堤防调度;在九江创办“妇婴庇护所”,收留逃婚避暴女子;于南昌主持首场“女性遗产仲裁庭”,判决一起百年世家争产案,裁定庶出女儿与嫡子同享继承权。
每下一令,必遭反弹。有人散布谣言,说她夜间召巫女做法,召唤“阴兵”镇压反对者;更有匿名檄文张贴街头,称其“貌美心毒,欲篡龙位”。但她始终不动声色,只将这些文字一一收录进《她说》的新卷,题为《诽我者言》。
某夜宿于庐山客栈,她独坐灯下翻阅旧稿,忽见一页夹着沈令月多年前写给她的信:
>“世人总以为我们争的是位置,其实我们争的是定义权??谁有权决定什么是正常、什么是规矩、什么叫做‘该’与‘不该’。”
她怔然良久,提笔续写道:“今日我所行之事,或许明日会被抹去名字。但我相信,总有一天,某个小女孩会在课本里读到这段历史,不会问‘她们怎么敢’,而是自然地说:‘原来她们一直都在。’”
抵达江南重镇姑苏时,已是初夏。此处富庶繁华,丝绸船队络绎不绝,却也是宗法最严之地。当地巨族陆氏世代垄断织造业,族规明文规定:“女子不得触机杼账目,违者沉塘。”燕宜一到,便接到数十名织娘联名控诉:她们日夜劳作,成果全归族中男丁所有,病倒即遭驱逐,甚至有人因要求结算工钱而被诬“通奸”投入祠堂幽禁。
她当即召集族老议事,出示《工律新条》:“凡劳动者,不论性别,皆享报酬权。阻挠者,罚没三成产业。”又宣布成立“织业公会”,由女工自行推选代表管理账目与分配。
陆家族长冷笑:“你可知我们陆家供养了多少读书人?多少官员出自门下?你敢动我,便是与整个士林为敌!”
燕宜淡然回应:“那我倒要看看,是你们的门生多,还是天下的织娘多。”
三日后,第一批分红发放。三百余名织娘齐聚广场,每人领到一张写有自己姓名的银票。许多人颤抖着不敢接,直到有人高喊:“这是我靠双手挣来的!我不怕!”
那一刻,掌声雷动,泪如雨下。
不久后,消息传回京城:姑苏女工集体上书,请求在全国推行“劳动凭证制度”,确保每一笔付出都有据可查。启明帝犹豫再三,终在沈令月力谏下允准试行。
秋风吹过江南,稻浪翻滚。燕宜站在田埂上,望着一群年轻女子驾驶改良犁具耕作,远处学堂传来童声诵读:“人生而平等,无论男女,皆有志学、谋生、参政之权。”她忽然觉得疲惫尽消,心中澄明如洗。
返京途中,她绕道探访“无夫谷”。昔日隐秘山洞已扩建为村落,百余名逃婚女子在此安居乐业,种茶养蚕,还办起了互助学堂。村口石碑刻着一行大字:“此处无夫,自有天理。”
一名白发老妪拄杖而来,正是当年那位靠背诵《楚辞》维持神志的才女。她如今已是村中学堂先生,每日教孩子们读诗写字。见到燕宜,她深深一拜:“大人,我终于活成了我想成为的人。”
燕宜扶起她,哽咽难语。
回到长安那日,雪花再度飘落。太极殿前,新铸的“她来军”军旗迎风猎猎,白莲徽记下,三百一十七个名字熠熠生辉。宫门外,数百名来自各地的女子静静等候??有女科进士、有商贾掌柜、有医馆大夫、有农会首领。她们并非请愿,只是想亲眼看看那个让她们能站在这里的人。
燕宜走下马车,风雪拂面,却不觉寒凉。
沈令月从宫门走出,递来一份诏书副本:“新设‘女子议政院’,隶属内阁,每年召开两次全国代表大会,审议涉及女性权益之法案。你是首任院长。”
她笑了,轻轻握住好友的手:“这不是结束,是刚开始。”
当晚,她在《她说》的最后一页写下结语:
>“这本书不会完结。因为它不属于我,也不属于这个时代。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沉默、如今开口的女子。我们的故事,才刚刚开始书写。”
窗外,春风将至,桃花含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