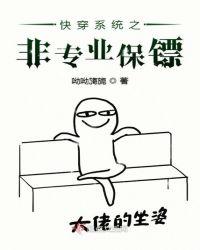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装傻三年:从状元郎到异姓王 > 第六百五十四章 成长(第2页)
第六百五十四章 成长(第2页)
夜里扎营,篝火燃起。阿禾盘膝而坐,双手贴地,开始“聆听”地脉。良久,她睁开眼,脸色凝重。
“下面有东西在挣扎。”她说,“不是记忆,是活体封印。它被困了很久,意识几乎溃散,但还在试图传递信息。”
沈知白立刻取出柳木笛,轻轻吹奏。笛声柔和,如同安抚婴儿的摇篮曲。片刻后,地面裂开一道细缝,一股暖流涌出,带着湿润泥土的气息。从中浮现出一块青铜残片,上面刻着古老文字:
**“勿信言王,其心已腐。归言国亡,非战之罪,乃信断也。”**
沈知白心头一凛。
“言王?”小女孩好奇地问。
“归言国最后一位执政者。”阿禾解释,“传说他本是贤君,但在外敌压境时,听信谗言,关闭了三座主塔,切断了全民共感网络。从此信任崩塌,人人自危,最终不战而亡。”
沈知白盯着残片,忽然意识到什么:“这不是历史记录……这是求救信号。那个被封印的存在,可能是当年反对言王决策的祭司之一,被当作叛徒镇压,却一直活着,等待真相重见天日。”
“我们要救他吗?”孩子问。
沈知白沉默良久,摇头:“不是救,是倾听。若他真是忠臣,他的痛苦本身就值得被听见;若他是阴谋者,我们也该知道,为何有人宁愿背负骂名也要抗争。”
于是众人围坐,以笛声为引,以童谣为媒,共同吟唱一段无词之歌。随着频率叠加,地下封印逐渐松动,一道苍老的声音透过地缝传来:
“我不是祭司……我是清洁工。”
众人愕然。
声音继续:“我每天打扫心声塔底层,听见所有人的秘密。我知道言王最初是真心为民,但他身边的人,一个个被恐惧吞噬。他们害怕共感太强,会失去自我;害怕别人窥探私情;害怕承担他人之痛……于是他们悄悄篡改共振频率,让塔变得迟钝。到最后,不是塔坏了,是人心先坏了。”
“那你为何被封印?”
“因为我告诉了一个孩子真相。第二天,全村人都说我是疯子。他们忘了共感的意义,只剩下对‘异类’的恐惧。我被拖进地穴,戴上禁言环,沉入永寂。”
沈知白闭上眼,胸口发闷。
多么讽刺。他们跋涉千里寻找火种,却发现毁灭早已始于内部。不是外敌太强,而是自己先放弃了相信的能力。
“你恨他们吗?”他问。
地底沉默许久,才答:“我不恨。我只是难过。难过到今天,还有人愿意来找我。”
沈知白起身,跪在裂缝前,郑重道:“我们听见你了。你的名字,不会消失。”
话音落下,青铜残片化作粉末,随风而逝。地面缓缓合拢,取而代之的是一株矮小植物破土而出??形似蒲公英,但种子呈泪滴状,散发柔和白光。
“这是……‘信籽’。”阿禾轻声道,“只要有人带着它离开,并在别处种下,就能重建局部共感场域。”
沈知白小心翼翼采下一枚种子,放入玉匣。
继续南行,穿越雨林。毒虫猛兽避之不及,仿佛感知到他们身上携带着某种古老秩序的气息。第七日,抵达南美亚马逊流域边缘。这里河道纵横,原始部落散居两岸,从未与外界通联。
当地土著起初持矛戒备,直到小女孩跑上前,用生涩的手势比划:“我们来找会唱歌的河。”
一名年迈酋长眯眼打量他们,忽然指向天空。此刻正值黄昏,云层裂开一线,阳光斜照河面,整条河水竟泛起粼粼金波,且随水流节奏起伏,发出类似竖琴的鸣响。
“神之喉。”酋长说,“三十年前干涸,今日复鸣,必因贵客至。”
当晚,部落举行祭祀。篝火熊熊,舞者赤身绘彩,围绕河岸旋转跳跃。沈知白注意到,每当舞步形成特定图案,河底便会升起一团光球,内中浮现影像:一群古人肩扛巨石,修建某种圆形祭坛,口中齐诵:
**“以血为契,以声为桥,连结万灵。”**
阿禾猛然抓住沈知白的手:“这不是归言国的技术!这是更早的文明??‘语源族’!他们是所有共感能量体系的源头!”
沈知白瞳孔收缩。他想起书中未曾解读的符号,那些看似装饰的纹路,竟是语源族的文字。而眼前仪式,正是激活地脉节点的方法。
“我们必须参与。”他说。
于是,在酋长允许下,沈知白吹响柳木笛,阿禾以手击地打出节拍,孩子们合唱那首来自南极胚胎实验室的旋律。三方频率交汇,河水骤然沸腾,一道巨大光柱冲天而起,直贯云霄。
光柱中心,缓缓降下一块水晶碑,碑文清晰可见:
**“第一守则:语言诞生于情感,而非逻辑。
第二守则:倾听比诉说更重要。
第三守则:当你想否定一个人,请先感受他的痛。”**