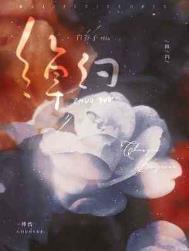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婚后上瘾 > 第392章 陆 魏 我对你很满意(第2页)
第392章 陆 魏 我对你很满意(第2页)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,随后郑重答应:“我代表国家承诺,这条写进试行办法第一条。”
挂断电话后,袁晨曦靠在椅背上,长长吐出一口气。她知道,这不仅仅是一次政策推动,更是一场价值观的博弈。过去多少类似项目轰轰烈烈开场,最后沦为形式主义的摆设?她不愿“回声”也成为其中之一。
中午,念安跟着保姆来到医院。小男孩一进门就扑向朵朵:“姐姐!我录视频啦!妈妈说全世界都能看见我!”
朵朵勉强笑了笑:“真厉害。”
念安却敏锐察觉到她的情绪,转头抱住袁晨曦的腿:“妈妈,姐姐为什么不开心?”
袁晨曦蹲下身,认真看着儿子的眼睛:“因为她心里很难过,就像下雨天没带伞一样。我们要做的,就是给她撑一把伞,陪她等到天晴。”
念安点点头,爬上床小心翼翼抱住朵朵:“姐姐,我不怕打雷,我可以陪你睡觉。”
简单的童言像一道暖流,击穿了朵朵最后一道防线。她抱着念安,低声啜泣起来。
下午两点,袁晨曦召集团队召开紧急会议。地点就在医院附近的咖啡厅包间。苏小梅、技术主管林舟、法律顾问陈然悉数到场。
“我们必须立刻启动‘守护者计划’。”她开门见山,“针对高危儿童建立三级预警机制:一级由学校老师上报异常行为;二级由区域心理观察员介入访谈;三级直接联动医疗与社工系统。”
林舟皱眉:“技术上可行,但我们目前的数据权限有限,很多学校担心隐私泄露不愿接入。”
“那就从自愿试点开始。”袁晨曦果断道,“第一批选十个最偏远但也最需要帮助的地区。设备我来协调基金会捐赠,师资培训同步跟进。”
陈然提醒:“法律层面也要配套。比如教师上报是否免责?心理档案如何保管?这些都要明确。”
“我已经草拟了《儿童心理危机干预权责指引》初稿。”袁晨曦翻开文件夹,“等会儿发给你们修改。另外,我要申请以个人名义发起专项基金,专用于高风险个案的紧急救助。”
会议结束已是傍晚。袁晨曦回到病房,发现朵朵正在画画。这次的画面不同以往??不再是孤独的身影,而是一座桥,桥两端站着两个女人,中间有个小女孩牵着她们的手。标题写着:《我想回家的路》。
“老师……我想试试看。”朵朵轻声说,“我不想死了……我想活着,好好活着。”
袁晨曦眼眶发热,紧紧抱住她:“太好了,朵朵。这才是我认识的那个勇敢的女孩。”
当晚,她在酒店房间写下一封公开信:
>致所有正在经历黑暗的孩子:
>
>我曾也是一个不敢说话的人。害怕被嘲笑,害怕被抛弃,害怕自己不够好。所以我懂你躲在角落里的样子,懂你用伤害自己来表达痛苦的方式。
>
>可我想告诉你:你的痛不是软弱,而是求救的信号。这个世界或许曾对你冷漠,但它不该因此剥夺你活下去的权利。
>
>“回声计划”不只是一个项目,它是一个承诺??无论你在哪里,无论你经历了什么,总会有人愿意听你说完一句话,陪你走过一段夜路。
>
>如果你现在正站在悬崖边,请抓住那只伸向你的手。哪怕那只手来自陌生人,也请相信,它是真实的。
>
>因为我们都在等你回来。
>
>??袁晨曦
第二天清晨,这封信连同朵朵的画(已匿名处理)一同发布。短短三小时内,转发量突破百万。无数网友留言:
【@月光下的树】:十年前我也割过腕,就是因为没人懂我。今天看完这封信,我哭了。谢谢你还愿意为我们说话。
【@山区教师阿杰】:我们班有个孩子,父母外出打工五年没回来。他每天写日记给“空气爸妈”,昨天交作业时写了句:“今天我又假装很开心。”我该怎么办?
袁晨曦立刻回复:“私信我,我们马上为你所在学校接入‘情绪信箱’系统。”
与此同时,一场悄无声息的变革正在发生。北京某重点中学率先宣布设立“心理安全日”,每月一天停课开展情感教育;广州一家大型企业主动联系“回声计划”,愿资助百名乡村儿童接受长期心理辅导;更有数十位明星联合发起“倾听一小时”公益活动,呼吁公众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