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迷阁>边关兵王: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> 第482章 戴罪之身(第1页)
第482章 戴罪之身(第1页)
“苏璃,你不是被朝廷发配到北疆充作罪女了吗?怎么还敢跑回神都?”宋清欢双手环抱胸前,下颌微抬,语气刻薄至极。
一旁的宋清泉立刻帮腔,嗤笑道:“就是!苏璃,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现在的身份!一个戴罪之身,也好意思踏我们宋家的门?你配吗?”
“放肆!”宋敬芝勃然变色,厉声呵斥,“她是你们二姑的亲生女儿,是你们的表姐!谁允许你们如此无礼说话的?”
“大伯,我们说的难道不是事实吗?”宋清欢毫不退让,脸上满是。。。。。。
雪落无声,疏勒城的冬夜静得如同沉入深井。沈昭立于心疾科院中那株枯槐之下,手中捧着一卷《归梦录》新抄本,纸页微黄,墨迹犹润。昨夜刚添了三十七篇百姓口述??有牧人讲述亡妻临终前攥着他手说“别怕黑”,有老兵回忆战后返乡只见老母坟头荒草萋萋,却仍每日扫墓做饭如她在世。这些话不美,也不神异,只是真实得令人胸闷。
阿箬披着狐裘走来,肩上落了一层薄雪。“乌尔汗昨夜写了第一篇。”她轻声道,“题为《母亲唤我乳名》。”
沈昭抬眼。
“他说,十年前龟兹陷落时,他随族人逃难,途中与母亲失散。后来听说她被唐军误作敌谍斩首示众。他恨这世间,恨音律不能传情,恨佛经无法救亲,于是发誓要以声引魂,让所有离散者‘在梦里团圆’。”
风掠过屋檐,铜铃轻响。
“可今晨他读到一位突厥妇人写的段落??她丈夫死于边战,儿子也被征入骑兵,但她每天清晨仍为两人摆碗筷,嘴里念叨:‘吃吧,凉了伤胃。’他说……他突然觉得,自己造的梦太冷了,暖不了人心,只会冻住灵魂。”
沈昭闭目片刻,将手中书卷递给她:“把这篇放在首页。”
阿箬接过,指尖微颤。“你真相信文字能胜刀兵?”
“不是文字。”他摇头,“是承认痛苦的存在。乌尔汗的错,不在思念母亲,而在拒绝接受她已不在。他用声音筑起幻境,实则是把自己关进了坟墓。而这些人写下记忆,并非为了复活死者,而是告诉活着的人:你可以哭,但还得吃饭;你可以痛,但还得走路。”
远处传来钟声,是夜话堂开讲的讯号。
自战事平息以来,每晚戌时,心疾科庭院都会点燃篝火,百姓围坐,轮流讲述过往创伤。起初无人开口,只余火噼啪作响。直到一名少女说起她在突骑施劫掠中失去双亲,每夜梦见父亲站在门口喊她回家,醒来却发现家中只剩断墙残瓦。她说:“我不敢忘他们,可我又怕记得太清会疯掉。”话毕,全场默然,继而有人抽泣,有人起身拥抱她。
自此,夜话不断。
沈昭与阿箬并肩走向堂前,沿途见孩童在雪地堆起小小坟包,插上木牌写着“阿爷眠此”。这是新习俗??不再焚香祭鬼,而是以土丘标记记忆,每年冬至添雪一杯,春分浇水一勺,谓之“养忆”。
堂内炭火正旺,老乐师已在抚琴试音,医官则在一旁熬煮安神汤。众人见沈昭进来,纷纷起身行礼,却被他抬手止住。
“今晚不讲别人的故事。”他说,“讲我的。”
满堂骤静。
“我八岁那年,母亲病逝于长安郊外驿站。她本是罪臣之女,因父谋逆牵连,贬为驿婢。我随她流放,靠捡柴换米度日。那年冬天特别冷,她咳血半月,无药可医。临终前一夜,她拉着我的手说:‘昭儿,娘对不起你,没能给你个家。’我说:‘您就是我的家。’她笑了,第二天清晨就断了气。”
火光映着他侧脸,轮廓分明如刀刻。
“我把她埋在驿站后山,用碎砖围了个小坟。守驿官说她是罪籍,不得立碑。我就在旁边种了一株野梅,每年开花一次,淡白如雪。十年后我重返旧地,那树已被雷劈倒,根部腐烂,再不见花。”
他顿了顿,声音低了几分。
“后来我学会吹笛,常奏《点灯照当下》,说是驱邪醒神,其实是为了压住心底那个声音??母亲叫我吃饭的声音。我以为只要我不听,就不会软弱。可当乌尔汗用同样的旋律勾出我的幻象时,我才明白:逃避记忆,才是真正的迷失。”
堂中鸦雀无声,唯有炭火爆裂一声轻响。
阿箬悄然起身,从箱中取出一只陶埙,递给身旁一名盲童。孩子摸索着接住,轻轻吹出一段不成调的呜咽声,像是风穿过废墟。
沈昭看着他,缓缓续道:“所以我不再怕听见她的声音了。我怕的是,若有一天所有人都不敢提逝者的名字,那他们才算真正死去。我们办夜话堂,印《归梦录》,不是为了疗伤,而是为了让‘记得’成为一种勇气。”
老乐师忽然拨动琴弦,奏起《娘不走》的前奏。医官低声跟唱,接着是阿箬,然后是角落里的老兵、抱着婴儿的妇人、断臂的戍卒……歌声渐渐汇聚,不高亢,也不悲切,只是平稳地流淌,像渠水绕田。
>“娘没走,她在灶前熬粥,
>米粒粘锅底,香味飘满屋。
>她没走,她在坟头种菜,
>泪水浇萝卜,咸得吃不下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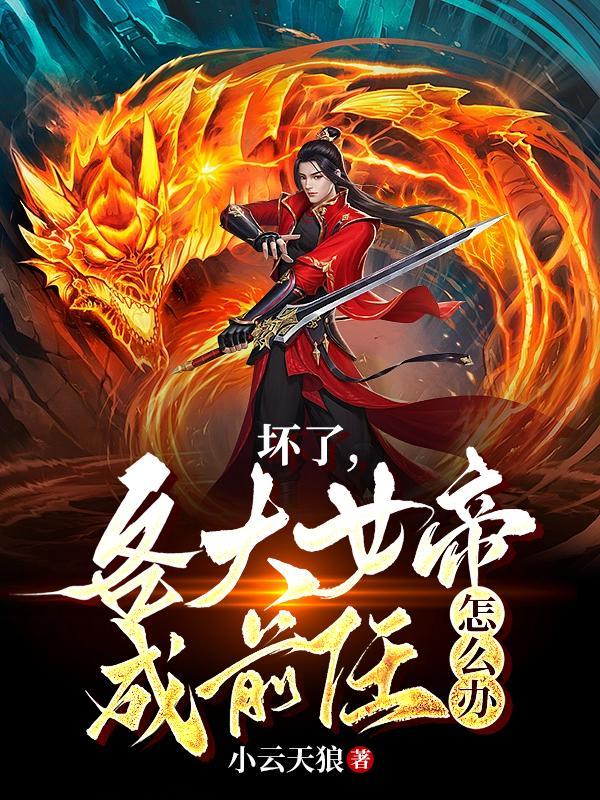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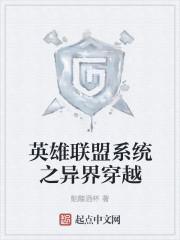
![七日逃生游戏[无限]](/img/31396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