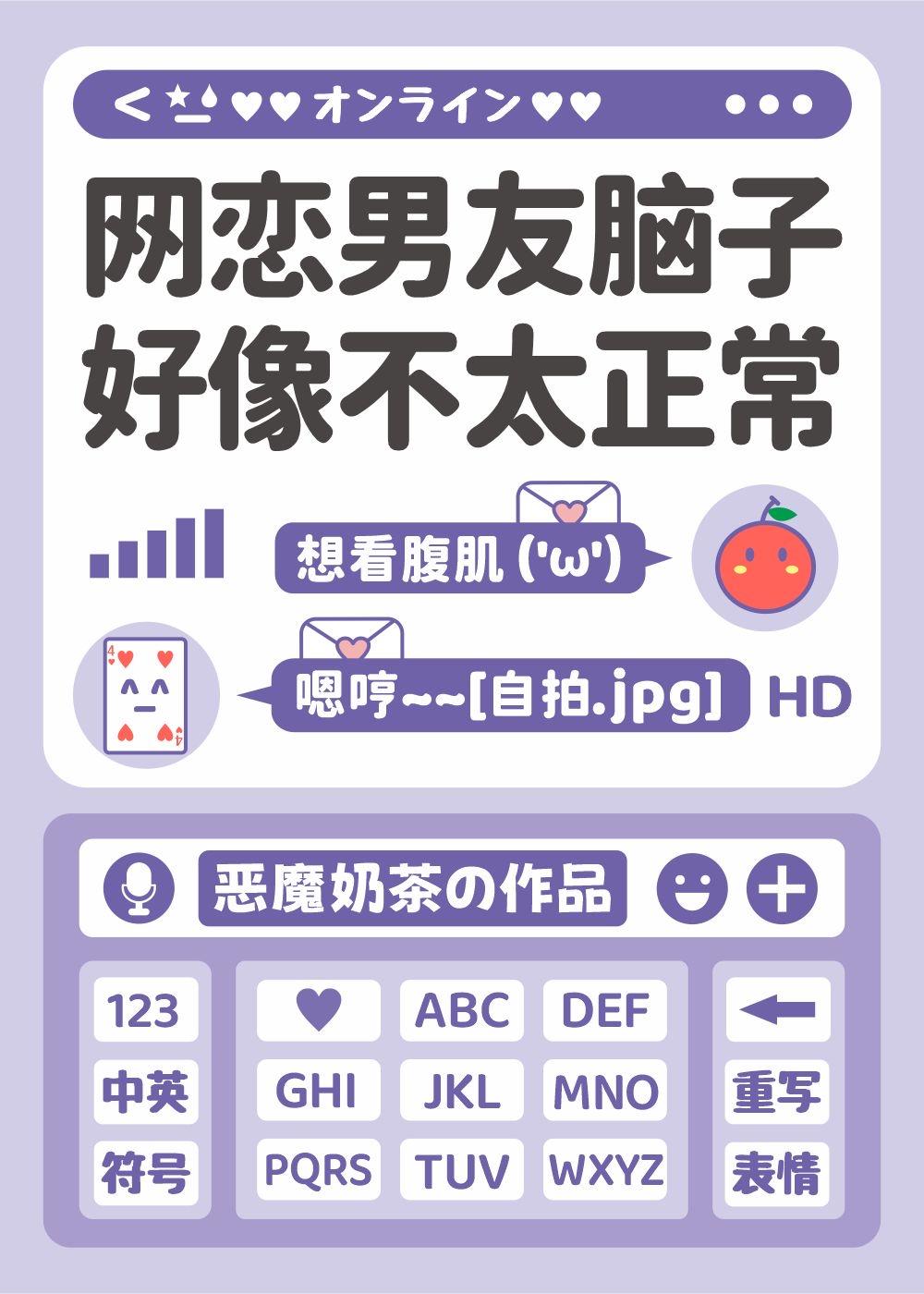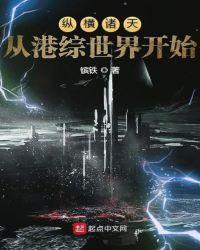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边关兵王:从领娶罪女开始崛起 > 第483章 提亲(第3页)
第483章 提亲(第3页)
第二年春,疏勒再度举办“归思节”。这一次,不仅汉民参与,突骑施、吐蕃、粟特乃至波斯商人都携族人前来。祭坛之上,九盏长明灯再次燃起,不同语言的祷告声交织在一起,形成一种奇异的和谐。
一名突厥少年将父亲的弯刀投入火中,哽咽道:“阿爸,你不回来了。但我学会了写字,以后每年清明,我都给你写一封信。”
一名吐蕃寡妇悬挂丈夫遗靴,轻唱家乡小调:“你走得太急,连鞋都没换。现在我把它洗干净,挂在风里,让它听见我想你。”
沈昭站在人群之外,静静看着这一切。阿箬走过来,轻轻握住他的手。
“你觉得裴渊会满意吗?”她问。
“他会说,这才刚刚开始。”沈昭微笑,“痛苦永远不会消失,但我们终于学会不躲它了。”
夏日某夜,暴雨突至。沈昭正在书房批阅公文,忽闻院外传来急促脚步。阿箬浑身湿透地冲进来,手中紧攥一瓶药液。
“你怎么……”
“我梦见你吹《折柳怨》。”她打断他,声音颤抖,“你在雨里一直吹,怎么叫都不停。醒来发现你在院子里站着,手里拿着笛子……虽然吹的是《点灯照当下》,可我还是怕……怕你其实在梦里。”
沈昭怔住。
他确实去了院子,也确实吹了笛子。但他以为没人看见。
“所以你带药来了?”
“是。”她点头,泪水混着雨水滑落,“如果有一天,你真的陷进去,我会亲手灌你。哪怕你恨我,我也要做。”
沈昭沉默许久,终于伸手接过药瓶,打开塞子,将液体缓缓倾倒入地。
“不用了。”他说,“我已经不怕听见她的声音了。我只怕有一天,再也听不见你的。”
阿箬扑进他怀里,放声大哭。
那一夜,雨声如鼓,敲打着屋瓦,也洗刷着旧日尘埃。而在城南的心疾科院中,一群年轻人正围坐在篝火旁,轮流讲述自己的创伤。轮到一名曾被梦引香控制的士兵时,他说道:
“我以为我会永远活在幻觉里。直到那天晚上,我听见一个女人在夜话堂说起她丈夫战死后,每天仍为他摆碗筷。她说:‘我知道他吃不到,但我得做,不然心会空。’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了??真实不是没有痛苦,而是明知无望,仍愿意付出一点温柔。”
火光映照着他脸上的疤痕,也照亮了周围一张张专注的脸庞。
他们不知道未来还会经历多少风雨,也不知道边关能否永久安宁。但他们知道,只要还有人敢说出“我记得”,只要还有人愿意为逝者摆一碗饭,只要还有人在雨夜里坚持吹响清醒的笛声??
那么,这片土地就不会真正荒芜。
冬去春来,黄沙依旧漫卷,驼铃声断续穿行于戈壁之间。某日清晨,一名牧童在城外拾得一枚锈迹斑斑的小铃,交予守城官兵。铃上依稀可见四字铭文:“听而不应”。
沈昭得知后,亲自前往查验。他摩挲着铃身,忽然一笑:“看来它完成了使命。”
他命人将铃悬于佛塔最高处,与其余十八枚并列。每当风吹过,十九铃齐鸣,声浪层层叠叠,宛如无数灵魂在低语:
>我记得。
>我痛过。
>我还在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