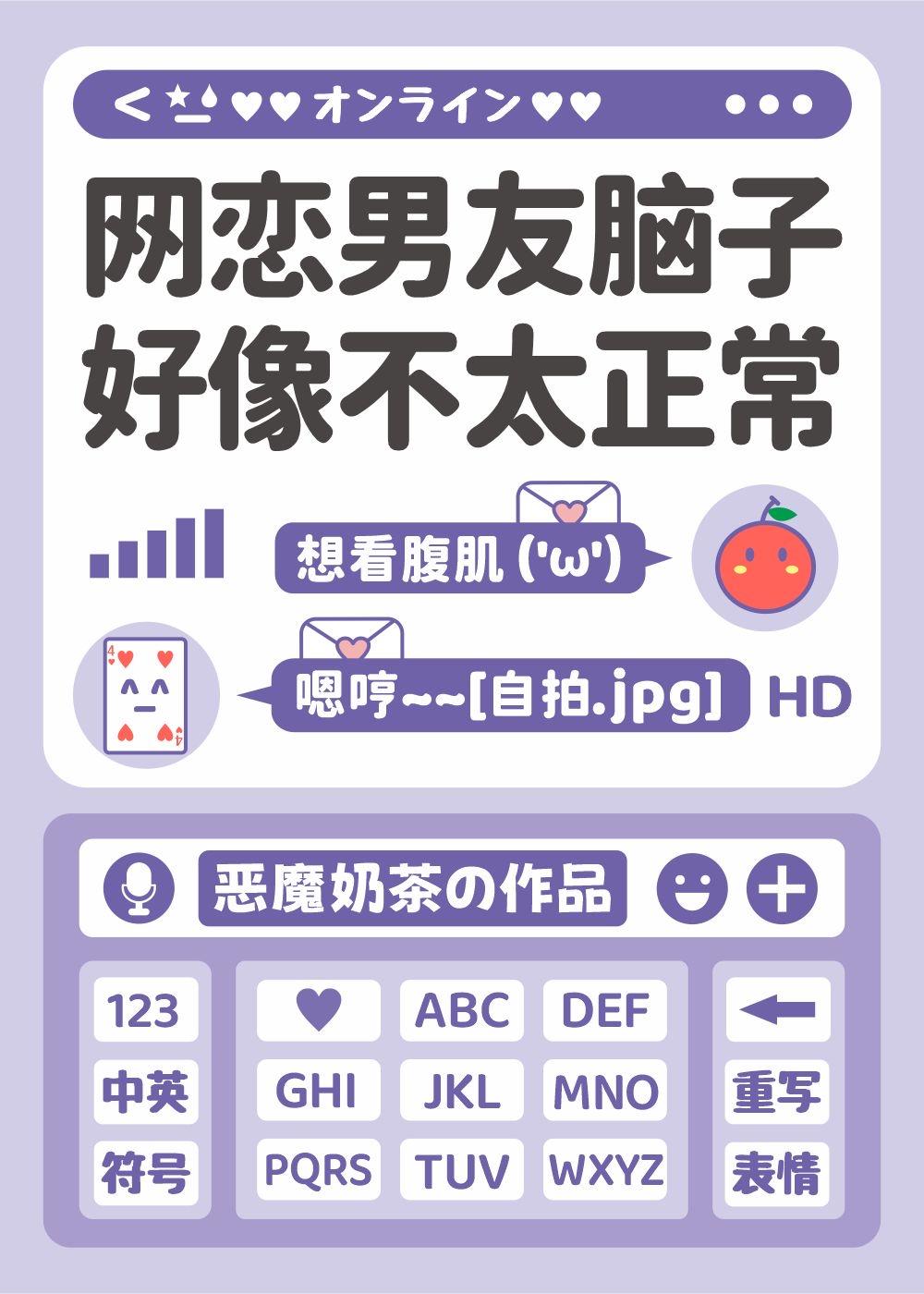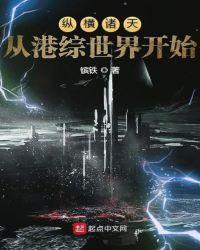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状元郎 > 第三二一章 大明魅魔(第1页)
第三二一章 大明魅魔(第1页)
当奢云珞和安贵荣的长子安万钟,带着整整十大车物资返回龙场驿时,便看到院子里已经整齐码放了好些新砖。
“这是哪里来的砖?”安万钟深感震惊,方圆百里应该一块砖都没有才对。
“我男人自己烧的呀。。。。
暴雨未至,殿内却已暗流汹涌。陈砚之松开手,指尖微凉,仿佛触到了蛇鳞。林景行退后半步,笑意依旧挂在脸上,可那双眼睛已悄然眯起,像猎人察觉陷阱边缘的动静。百官寒暄声中,谁也没注意这短暂的一握竟如刀锋相碰,无声却见血。
陈砚之退回班列,袖中手指紧攥着那枚从阿福处得来的铜印??父亲生前私章,刻着“清慎”二字。此印从未用于公文,却是他亲笔书信、密件封缄时所用。而今,它将作为最关键的物证,在风暴来临前静静蛰伏。
散朝后,他并未回府。新赐的宅院尚未修缮,他也不愿住进那象征荣耀的居所。他绕道西市,寻了一家不起眼的茶肆,坐在角落,点了一壶苦丁。不多时,一个挑担小贩模样的人推门而入,帽檐压得极低,径直走到他桌前,放下扁担,低声唤道:“陈公子。”
是李承允旧日仆从李三,忠厚老实,曾随主奔波于六部之间送信跑腿。如今主人已逝,他却仍守着一份情义。
“你来了。”陈砚之不动声色,“徐少卿可曾收到消息?”
李三摇头:“小人不敢贸然登门。只听街坊说,徐大人这几日告病不出,府上闭门谢客。倒是昨儿夜里,有辆黑篷马车停在巷口,直到天明才走。”
陈砚之眸光一凝。徐正言若真被监视,便不能再贸然接触。他沉吟片刻,从怀中取出一封密封的油纸信函,递过去:“你设法交给徐府老管家,就说……是故人遗物托付,务必亲手交到徐大人手中。切记,不可露面,不可留名。”
李三接过,重重点头,转身离去。
雨终于落了下来,先是细密如针,继而倾盆如注。陈砚之在茶肆坐到黄昏,听着檐下雨声敲打青石板,思绪翻腾。他知道,自己已踏入一张巨网之中,每一步都可能万劫不复。但李承允的死让他明白:沉默即是死亡,退让便是覆灭。
夜深人静,他悄然返回暂居的小院。刚推门,忽觉屋内气息不对??有人来过。
他立即熄灯,贴墙而立,耳听八方。屋内无动静,但他瞥见书案上砚台位置略有偏移,桌上尘灰亦有指痕。有人翻过他的东西!而且动作极快,未及细搜便离去。
他蹲下身,检查床底暗格。铁箱仍在,锁扣完好。他松了口气,随即又皱眉??箱角沾着一点湿泥,颜色偏红,似岭南山地特有。
有人跟踪他回来?
他猛然想起回京途中,在湘江渡口歇脚那一夜。当时风雨交加,驿站人满为患,他曾与一名背药篓的老者共宿一室。那人言语不多,只道是采药郎中,次日清晨便匆匆离去。如今想来,那人身形虽佝偻,脚步却稳健异常,且右手虎口有茧,分明是常年握刀之人。
刺客。
陈砚之冷汗涔涔。对方不仅知道他南下,还一路尾随,甚至在他归来前便先一步潜入住所探查。这意味着什么?意味着林景行早已布下天罗地网,只等他自投罗网。
但他也发现一线生机??对方并未动铁箱。说明他们还不知证据所在,或至少不确定。
翌日清晨,圣旨再下:新科进士需于七日后撰写《策论辑要》,呈内阁评定,优者可授编修,参与实录修撰。此乃惯例,却也是陈砚之等待的机会。
他提笔回忆父亲日记中的细节,结合李承允抄录的档案、阿福提供的证词,开始撰写一篇名为《科场积弊考》的策论。表面探讨历朝科举弊端,实则层层剥茧,引出嘉?六年舞弊案疑点,尤其着重分析“监试印裂痕”、“文章风格悖逆”、“主审官员突遭构陷”三大矛盾,并隐晦指出“有寒门出身之权臣,借清廉之名,行倾轧之实”。
他字斟句酌,既不失学者风范,又埋下足够线索。只要徐正言读到此文,必能会意。
七日后,策论交至内阁。当值学士正是林景行。他接过陈砚之的卷册时,嘴角含笑,眼神却如鹰隼扫过纸面。阅毕,他轻轻合上,对身旁同僚道:“陈修撰文采斐然,见解独到,可惜过于激切,恐伤和气。”
当晚,内阁传出风声:陈砚之策论“议论乖张,有碍纲常”,建议搁置不用,不予刊行。
陈砚之冷笑。他知道,这是打压的开始。
果然,第三日早朝,御史台一名言官出列弹劾:“翰林修撰陈砚之,身为新科状元,不思报效君恩,反撰文影射先帝,诋毁朝政,其心可诛!”奏章洋洋洒洒,列举数条“罪证”,皆出自《科场积弊考》中断章取义之语。
皇帝眉头微皱,未即表态,只命内阁议处。
退朝后,陈砚之被召入文华殿。殿中只有皇帝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德全。天子端坐御座,目光深邃:“陈卿,你可知罪?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