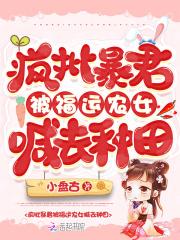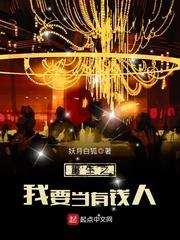书迷阁>状元郎 > 第三二一章 大明魅魔(第2页)
第三二一章 大明魅魔(第2页)
陈砚之跪地叩首:“臣无罪。所著之文,皆为考据史实,旨在警醒后人,杜绝科场舞弊,以保取士公正。若有冒犯之处,愿请斧钺。”
皇帝沉默良久,忽然道:“你父陈恪,曾任礼部右侍郎,为人刚正,朕记得他。”
陈砚之心头一震,抬头看向帝王。
“他不该死。”皇帝缓缓说道,“他是替别人背了罪。”
殿内烛火轻晃,映得龙袍上的金线微微发亮。陈砚之呼吸几乎停滞。
“朕那时年少,新政初行,朝中派系纷争激烈。有人欲借科场弊案清洗异己,你父因不肯同流合污,成了牺牲品。林景行……本是宰相门客,手段狠辣,善于借刀杀人。他伪造试卷,栽赃嫁祸,又买通证人,逼你父认罪。朕后来查觉蹊跷,然木已成舟,若再翻案,恐动摇国本,只得隐忍。”
陈砚之双目含泪:“陛下……既然知情,为何不为家父昭雪?”
“因为时机未到。”皇帝目光如炬,“林景行如今执掌贡举,党羽遍布六部,连军机处都有他的眼线。若贸然动手,只会引发朝局动荡。朕等了十年,就是在等一个能打破僵局的人??而你,就是那个人。”
陈砚之浑身颤抖,不是因为恐惧,而是因为希望。
“朕不能明着帮你,但可以给你三次机会。第一,大理寺本月将重审一桩旧案,涉及十年前护城河浮尸案。你可设法推动此案重启调查。第二,徐正言已被任命为刑部会审副使,你若有机缘,可与之密谈。第三……”皇帝顿了顿,“七日后,朕将亲临国子监讲学,你若能在众儒生面前,当众提出科场公正之问,朕自会回应。”
陈砚之重重叩首:“臣,遵旨!”
离殿时,王德全悄然递来一枚玉佩:“陛下说,若遇生死关头,持此物可入禁中面圣,守卫不得阻拦。”
陈砚之将玉佩藏入贴身衣袋,走出宫门,只见乌云渐散,晨光破晓。
他立刻赶往大理寺。护城河浮尸案正是周大勇之死,当年草草结案,称其“醉酒溺亡”。如今有了皇帝默许,他找到负责卷宗的小吏,出示父亲铜印与阿福手书证词,恳请重审。
小吏犹豫再三,终被他说动,答应上报。三日后,大理寺正式立案复查。
与此同时,陈砚之借修撰之职,频繁出入国史馆,查阅嘉?年间档案。他发现,当年参与监考的誊录官中,有一人名叫吴铭,原籍浙江绍兴,后调任福建,如今已致仕归乡。更巧的是,此人曾在日记中提及“林公赠金二百,谢我不言往事”。
陈砚之立即修书一封,请地方官协助传唤吴铭进京作证。同时,他通过李三联络徐正言。几经周折,终于在一个深夜,于城外荒庙相见。
徐正言年近五旬,须发微白,神情肃穆。听完陈砚之陈述,他久久不语,末了才道:“你可知我为何与林氏有怨?十年前,我妹夫亦因举报其贪墨遭陷害,流放岭南,途中暴卒。我查过,正是林景行授意。”
他取出一份密档:“这是我暗中搜集的证据,包括林党收受贿赂、操纵乡试名录的账册副本。再加上你的材料,足可掀起滔天巨浪。”
两人约定,待吴铭到京、周案重审有果,便联名上奏。
然而,就在第五日清晨,噩耗传来:吴铭所乘官船在鄱阳湖沉没,尸体至今未寻。地方报称“遭遇风浪”,但船上随从仅一人幸存,醒来后却疯癫失语,口中只反复念叨“火……火烧起来了……”。
陈砚之怒极反笑。又是“意外”?天下哪有这般多巧合!
他不再等待,决定提前行动。
七日后,国子监讲学日。皇帝驾临辟雍殿,三千学子列席听讲。讲毕经义,皇帝照例询问诸生有何疑问。
陈砚之起身,整冠敛袖,朗声道:“臣有一问,关乎天下士子之心。”
全场寂静。
“嘉?六年,礼部贡院发生舞弊案,副主考陈恪大人蒙冤自尽。十年来,真相湮没,黑白颠倒。今日臣斗胆请问陛下:科举取士,究竟为选贤任能,还是为权贵遮羞?若一名清官因坚持公正而死,而真正的舞弊者却步步高升,那这金榜题名,又有何意义?”
话音落下,满堂哗然。
林景行脸色铁青,欲起身斥责,却被身旁老臣按住肩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