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迷阁>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> 房陵困顿(第2页)
房陵困顿(第2页)
一日,赵楷在州城外的集市上闲逛,看到一群乡民围着一个铁匠铺争吵。原来,是附近山村的村民拿来几把损坏严重的农具——锄头、镰刀等,要求铁匠修复。但铁匠铺设备简陋,技术落后,只能进行简单的锻打修补,对于已经卷刃、开裂严重的铁器无能为力。村民抱怨铁匠手艺差,铁匠则抱怨村民的铁料太次,双方争执不下。
赵楷在一旁观察良久。他发现,问题的核心依旧是材料和热处理。这些农具用的都是劣质生铁,韧性差,硬度不足,极易损坏。而铁匠的修补只是表面功夫,无法从根本上改善性能。
一个念头闪过:他能不能帮帮忙?虽然他没有将作监的先进设备,但基础的热处理原理他是懂的!或许可以用土法尝试一下?
他走上前去,表明了自己“团练副使”的身份(虽然没啥用,但好歹是个官身),询问情况。
村民和铁匠见是官员,态度恭敬了些,诉说了各自的难处。
赵楷检查了那些破损的农具,对铁匠说:“老丈,你这些家什,修补固然可以,但用不了多久还会坏。关键在于铁料本身不行,淬火之法亦不得当。”
老铁匠闻言,有些不服气,但又不敢顶撞官员,嘟囔道:“大人明鉴,小老儿世代打铁,皆是这般手法。这山里的铁料,本就如此,能有甚法子?”
赵楷笑了笑,说道:“我或许有个土法子,可以试试改善这铁器的韧性,让其更耐用些。可否借你的炉火一用?”
老铁匠将信将疑,但官命难违,只得让出位置。
赵楷让铁蛋帮忙拉风箱,控制火候。他挑选了一把缺口不大的旧锄头,放入炉中加热。他没有追求高温,而是仔细观察铁器的颜色变化,判断其达到了一种相对均匀的“奥氏体化”温度(他心中的概念)。然后,他迅速将锄头夹出,不是立刻放入水中淬火,而是先在空中短暂停留,让其温度稍微下降一点(类似正火或退火的前期),然后再放入一旁准备好的温热盐水中淬火。
这是他根据现有条件,能想到的最简单的“改善韧性和硬度平衡”的土办法。控制加热温度和冷却速度是关键。
淬火完成后,锄头表面覆盖着一层氧化皮。赵楷又将其回火(用炉火的余热稍微烘烤),以消除内应力。
整个过程,周围的村民和老铁匠都看得目瞪口呆,不明觉厉。
最后,赵楷将处理过的锄头打磨了一下,递给村民:“你试试看,是否比原来强韧些?”
村民半信半疑地接过,用力掰了掰锄头刃口,惊讶地发现,弹性似乎真的好了很多,不像原来那样脆硬!他又用石头敲击,刃口也没有崩裂!
“神了!神了!”村民惊呼道,“大人真是神技!这锄头好像……变结实了!”
老铁匠也凑过来仔细查看,用手触摸,感受那不同的质感,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。他打了一辈子铁,从未见过如此神奇的手法!
“大人……您这……是何仙法?”老铁匠颤声问道。
赵楷摆摆手,笑道:“非是仙法,不过是些……嗯……‘火候’的窍门罢了。你若想学,我可以教你。”
老铁匠扑通一声跪下了:“求大人传授!小老儿愿拜大人为师!”
就这样,赵楷在这偏远的房州,意外地收获了他的第一个“技术学徒”——一位姓张的老铁匠。
此后,赵楷便时常光顾张铁匠的铺子,指点他一些基本的选料、锻造和热处理技巧。虽然条件简陋,无法实现精密控制,但仅仅是优化加热时间、尝试不同的淬火介质(水、油、盐水)、增加回火工序等简单改进,就使得张铁匠打造和修复的农具质量显著提升,变得更加耐用。
消息很快在附近的乡民中传开:“州城里来了个赵大人,会点金术!经他手点拨过的铁家伙,结实又好用!”
来找张铁匠打制、修复农具的人越来越多,甚至还有其他乡镇的铁匠慕名而来,想要求教。
赵楷来者不拒。他反正闲来无事,便将改善农具作为一个小小的“项目”。他不仅指导热处理,还尝试优化农具的形制,比如根据本地土质和作物特点,设计更省力、效率更高的锄头、镰刀形状,并让张铁匠试着打造。
他还注意到,本地缺乏有效的粮食加工工具。石磨效率低下,舂米费力。他尝试指导木匠和石匠合作,制作了一种结构更合理的手摇式石磨和杠杆式脚踏碓,虽然粗糙,但确实提高了效率。
这些技术扩散虽然缓慢,影响范围有限,却实实在在地改善了一小部分当地百姓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。赵楷在这个过程中,重新找到了自身价值的存在感。他不再是那个无所事事的“贬官”,而是能用自己的知识,为这片土地和人民做点实事的“赵先生”。
科技树,没有死去。它只是在新的、更艰苦的环境中,以一种更朴素、更贴近土地的方式,顽强地重新萌发出了稚嫩的绿芽。
然而,赵楷并不知道,他在这偏远之地的这些“小打小闹”,虽然低调,却并未完全逃过某些有心人的眼睛。一场新的风波,正在悄然酝酿。而这一次,风波的中心,竟然是他无意中改良的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农具和加工工具。
平静的房州生活,似乎即将被打破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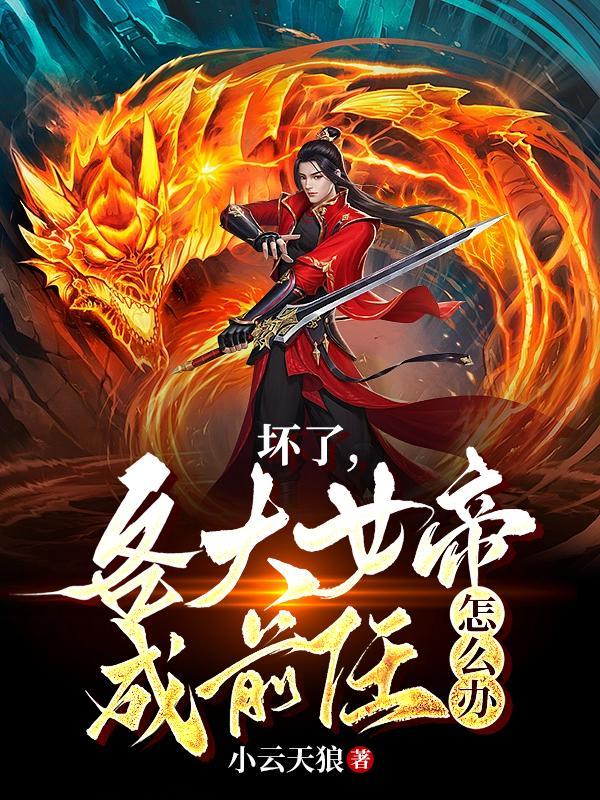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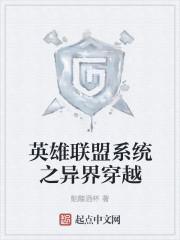
![七日逃生游戏[无限]](/img/31396.jpg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