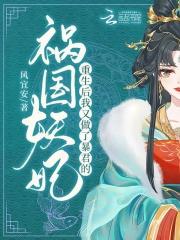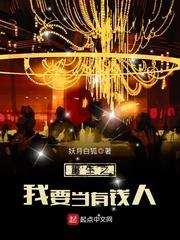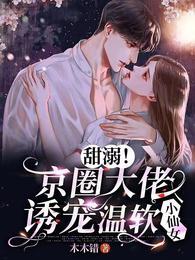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本王的科技树长歪了 > 新朝风雨(第2页)
新朝风雨(第2页)
调查了一圈,得到的都是些模棱两可、无法坐实罪名的信息。
刘知州便据此写了一份回文,大意是:经查,赵楷初至房州时,确与匠人有所往来,探讨农具改良,然其心似在惠民,并无滋扰之举,且其法于农事略有裨益。后经州衙劝导,赵楷已深居简出,安分守己,未见异常。至于“擅改祖制”、“心怀怨望”等事,查无实据。
这份回文,既承认了赵楷有过“不安分”的行为(给上头一个交代),又强调其已改正且无大恶(替赵楷开脱),最后以“查无实据”结案(规避风险)。典型的官场文章。
公文上报后,汴京那边暂时没了动静。显然,王貺等人想凭这点“小过错”就扳倒一个宗室,在新朝初立、求稳为主的大背景下,并不容易。御史台也需要更确凿的证据。
第一次风暴,被刘知州的“和稀泥”战术暂时挡了过去。
赵楷得知消息,稍稍松了口气,但不敢有丝毫大意。他知道,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。
果然,数月后,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。这次,对方改变了策略,不再纠缠于“农具风波”,而是将矛头指向了赵楷的出身和在汴京的“旧账”。
有御史联合上疏,旧事重提,再次抨击赵楷在将作监推行“标准化”是“墨家余孽”、“机械之心”、“败坏匠德”,并声称其与狄明月“过往甚密,有损宗室清誉”,甚至隐隐牵连到曹玮“用人不明”。奏疏要求新君“肃清朝纲,清退佞幸”,将赵楷这类“幸进之徒”彻底逐出朝堂,以正视听。
这一招更为阴险恶毒,直接攻击赵楷的立身之本和人际关系,试图在新君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。
消息传到房州,赵楷的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。这一关,远比第一关更难渡过!因为这涉及的是意识形态和政治站队问题,是新君树立权威时可能用来祭旗的绝佳目标!
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慌。这一次,刘知州恐怕也回护不了他了!
就在他几乎绝望之际,汴京传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——狄明月通过秘密渠道送来口信:曹皇后(现为皇太后)在关键时刻,出面保下了曹玮和狄青,并委婉地向新君进言,称赵楷虽有行为乖张之处,然其心在公,于军械亦有微功,且为宗室远支,不宜轻废,可令其闭门思过,以观后效。
皇太后出手了!
赵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!曹太后(之前的曹皇后)竟然会为他说话!虽然言辞谨慎,只是“保其不死”,但在这风口浪尖上,这无疑是救命稻草!
他瞬间明白了其中的关窍。新君赵曙并非曹太后亲生,即位之初,地位未稳,需要安抚和依靠以曹太后、曹玮为代表的部分旧臣势力。曹太后此举,既是在维护旧臣体系(曹玮、狄青),也是在向新君展示其影响力,是一种政治平衡。而保下赵楷这个“小角色”,不过是顺手为之,既全了旧情(曹玮的面子),也显得宽厚,更不会触动核心利益。
政治,永远是权衡和妥协的艺术。
无论如何,曹太后的干预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新君赵曙最终采纳了太后的建议,对赵楷一案做出了裁决:赵楷行事确有不当,然念其宗室之亲,且于军械薄有微劳,着革去房州团练副使之职,贬为庶人,禁锢于房州居住,非诏不得离境,以儆效尤。
旨意传到房州,赵楷跪接圣旨,心中百感交集。
革职!贬为庶人!禁锢!
这意味着他失去了最后的官身,成了一个被软禁在房州的平民宗室,政治生命彻底终结。
然而,保住了性命!没有被流放更恶劣的烟瘴之地,没有被投入大牢!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!
刘知州等人也松了口气,只要不闹出人命,不牵连自己,怎么都好说。
赵楷的“蛰伏”策略,加上曹太后关键时刻的出手,终于让他在新朝的腥风血雨中,惊险地保住了一丝生机。
风波暂时平息。赵楷真正成了房州的一个“闲人”,一个被圈禁的“宗室庶人”。他的活动范围更小,处境更加艰难。
但他并没有彻底绝望。只要还活着,只要还能思考,只要他那颗“歪楼”的心不死,就还有希望。
他变得更加低调,几乎足不出户。但他并没有停止学习和思考。他让铁蛋想方设法从外面搜罗各种书籍,不仅是经史子集,更多的是杂记、农书、医书、工巧之作,甚至是一些流传不广的域外奇谈。
他不再直接动手制作任何东西,而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知识的积累和理论的梳理上。他将自己在汴京将作监的经历、在房州的实践、以及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,结合前世模糊的记忆,开始系统地整理和撰写笔记。
他撰写关于材料性能的观察记录,关于简单机械原理的推演,关于标准化度量衡的设想,关于农业工具改良的构思,甚至开始尝试用极其简陋的数学工具,去推演一些基础力学和热学现象。
他将这些笔记加密,分散藏匿。他知道,这些知识在当下可能毫无用处,甚至是“异端邪说”,但它们是他科技树的种子和根系。只要根还在,一旦遇到合适的土壤和气候,就有可能再次萌发。
蛰伏,是为了更深的扎根。
在漫长的禁锢岁月里,科技树以一种外人无法察觉的方式,在思想的深处,悄然生长着。它不再追求枝叶的外显,而是转向根基的深厚和理论的沉淀。
赵楷并不知道,他这种看似徒劳的“纸上谈兵”,在未来的某一天,会以怎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,重新焕发生机。
而命运的转折,往往就隐藏在最深的绝望和最长久的等待之后。房州的寒冬,似乎格外漫长,但春天的讯息,或许已在远方的地平线上,悄然孕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