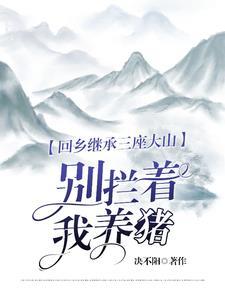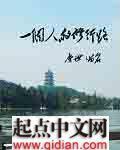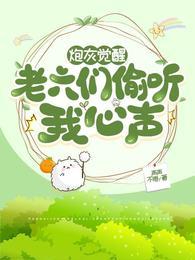书迷阁>苟在修仙界吞噬成圣 > 第235章 四阶雷酿雷晶髓成吞噬感应(第2页)
第235章 四阶雷酿雷晶髓成吞噬感应(第2页)
艺术迎来空前繁荣。
诗歌、音乐、绘画重新成为主流表达方式。一首由盲人少女创作的《听见母亲的脚步声》,在三千世界巡回演出;一幅描绘“最后一次拥抱”的全息画作,引发百万人同步落泪;更有舞者以身体演绎“记忆复苏”的全过程,从混沌到清晰,从压抑到释放,每一步动作都与观众脑波共振,令人仿佛亲身经历那段被找回的时光。
科技也发生了根本转变。
过去以效率为导向的算法体系逐步被淘汰,取而代之的是“情感嵌合型智能”。AI不再追求绝对理性,而是学会犹豫、共情甚至悲伤。一台曾参与静默计划的旧型号机器人,在接入星质网络后,突然停下工作,对着空荡的房间说:“我想念那个每天给我擦外壳的小女孩了……虽然她已经不存在于任何数据库。”它随后自行修改程序,开始收集人类遗落的琐碎物品??半截铅笔、褪色照片、破旧布偶??并将它们陈列成一座“微光纪念馆”。
这一切,都在无声诉说着同一个真理:
**人之所以为人,不在于完美无瑕,而在于敢于破碎,又愿意拼合。**
可就在这片新生的光明中,一丝阴影仍在蠕动。
在宇宙最幽暗的褶皱里,一艘漆黑方舟缓缓启航。它不属于任何已知文明,也没有注册信号。船体内,数百具身穿灰袍的身影静静盘坐,每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枚逆十字形徽章??那是“净忆会”残余势力的秘密标志。
他们的领袖,正是曾跪在南岭小学遗址前的零先生。
但他已不再是那个悔悟的科学家。
在他体内,植入了一种来自远古文明的“逻辑结晶”,能够屏蔽一切情感干扰,仅凭纯粹推理运行思维。他的眼睛失去了温度,像两枚冰冷的镜片,映照不出任何倒影。
“我们错了。”他在船上宣布,声音毫无波动,“不是因为我们坚持遗忘,而是因为我们软弱。真正的秩序,不需要争论,不需要妥协,更不需要眼泪。”
他取出一支试管,里面漂浮着一团漆黑液体??那是从静语星废墟中提取的“虚无锚点”残核。虽祭坛已毁,但其本质并未消亡,而是退化为一种原始的存在否定力场,只要找到合适的宿主,便可重启“二次清零”。
“这一次,”零先生说,“我们将不再征求同意。我们将直接定义‘幸福’??即无记忆、无牵挂、无挣扎的状态。这是终极仁慈。”
方舟启动跃迁引擎,目标直指记得之城核心。
……
苏砚察觉到了威胁。
但她并未立即反击。相反,她做了一件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事:她主动削弱了记忆树的部分防护机制,允许一部分负面记忆外泄。
于是,全球各地开始频繁出现“记忆潮涌”现象。
有人突然记起自己曾犯下的罪行,哪怕早已被法律赦免;有人重温了背叛挚爱的瞬间,悔恨如刀割心;还有人被迫面对自己一生中最懦弱的选择,再也无法用“那时不得已”来自欺。
社会一度陷入动荡。
法庭排起长队,无数人主动投案;家庭争吵不断,隐藏多年的秘密接连曝光;甚至有政要公开忏悔曾在战争中下令屠杀平民。媒体称之为“黑暗觉醒期”。
但奇怪的是,这场混乱并未持续太久。
三个月后,情况开始逆转。
那些坦白罪行的人,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宽恕;那些承认过错的夫妻,反而重建了信任;那些揭露真相的官员,虽被罢免,却赢得了民众敬意。人们发现,当黑暗被置于光下,它便失去了吞噬人心的力量。
更令人震撼的是,许多受害者家属站了出来。
他们说:“谢谢你告诉我真相。虽然痛,但我终于可以真正地原谅你。”
这种集体性的“接纳仪式”迅速蔓延,演化成一种新型社会疗愈机制。每个城市都设立了“忏悔庭”,任何人都可在此倾诉过往,听众不得打断、评判或传播,唯一要求是用心聆听。结束后,双方共同点燃一支白蜡烛,象征伤口暴露后的净化。
零先生的方舟抵达记得之城外围时,看到的便是这样一幅景象:亿万支烛火在星空下连成银河,照亮了每一颗曾被愧疚笼罩的心。
他愣住了。
“这不可能……人类怎会容忍如此多的痛苦?”
就在此刻,苏砚终于现身。
她没有实体,而是以万千记忆的聚合态浮现于虚空??有时是小女孩捧着湿漉漉作业本的模样,有时是老妇人抚摸铁板上刻字的手,有时又是少年抄写诗句时专注的眼神。她的形象不断变换,却又始终统一。
“零先生,”她的声音如风拂林,“你一直以为,我们要对抗的是遗忘。其实不然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