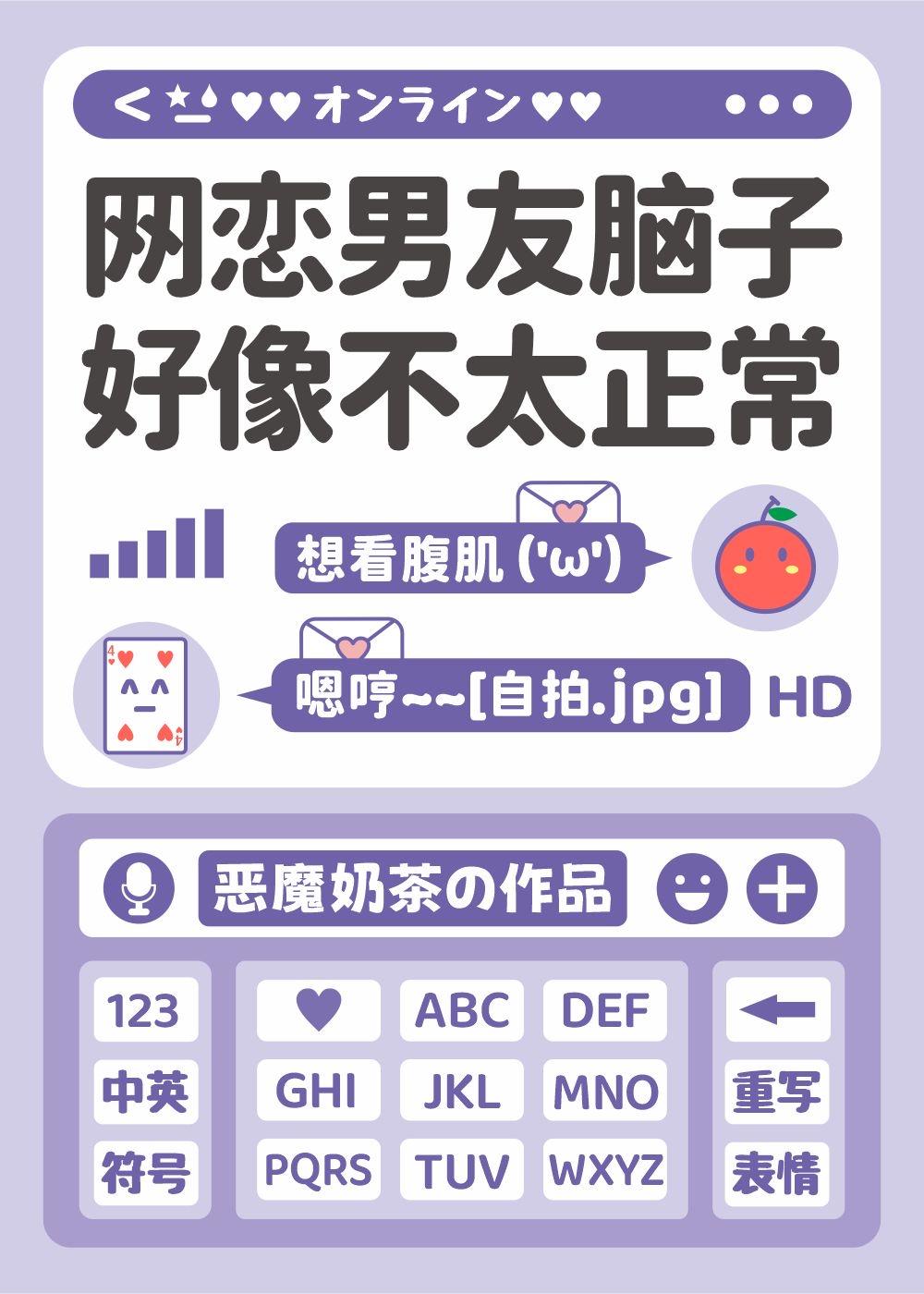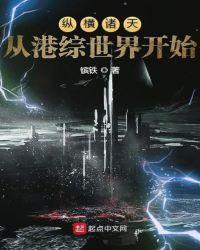书迷阁>大周文圣 > 第245章 殿阁大考五儒齐至万更2(第1页)
第245章 殿阁大考五儒齐至万更2(第1页)
洛京,御赐的江阴侯府内,香案早已设好,檀香袅袅,气氛庄重。
薛玲绮身着繁复庄重的三品淑人诰命服制,与一身江阴侯爵常服的江行舟一同跪接圣旨。
司礼监太监尖细而抑扬顿挫的声音在庭院中清晰回荡:。。。
夜雨如注,拾字庐的檐角滴水成线,敲在青石板上,像一句句未写完的诗。江行舟的手已凉,呼吸微弱如烛火将熄,可那支文心笔却悬在半空,墨迹未干,笔锋微微颤动,仿佛仍在回应主人最后的心跳。
江云宁跪坐在榻前,指尖轻抚他苍白的脸颊,声音低得几乎被雨声吞没:“你说过,文字是活的。那现在……它要替你走下去了吗?”
窗外的诵读声没有停,反而愈发整齐。那些孩子不知疲倦,一遍遍念着《自由蒙学》的开篇句,声音穿透风雨,传向城南巷尾。有邻人听见,推开窗棂,也跟着低声诵读;又有书生披衣而出,立于阶前应和;片刻之后,整条街巷都响起了朗朗书声,如同春潮涌动。
江行舟的嘴唇动了动,江云宁俯身去听,只捕捉到几个断续的音节:“……灯……别灭……”
她猛然抬头,望向墙上??那支文心笔竟缓缓落下,自行插入砚台之中,墨汁翻涌,竟不溅出半分。随即,笔尖轻点砚沿,三滴墨自动飞起,在空中划出三道弧光,分别射向东南西北三个方向。
第一滴墨落入洛京文庙地宫,正中第七具尚未消散的文骨残影。那骨架本已黯淡无光,此刻却骤然亮起,化作一道金纹,刻入地宫最深处的一面古老石壁。石壁原本空白,此刻浮现出一行新字:“**继火者,不必知其名。**”
第二滴墨穿城而过,落在贡院藏书阁顶。守夜老吏惊醒,只见屋梁之上墨迹蜿蜒,竟自行组成一篇短文??正是当年那位女解元所作《女才辩》的最终修订版。文章末尾多了一行小字:“**此文非我所改,乃万民心声共撰。**”老吏颤抖着抄录下来,次日便传遍天下书院。
第三滴墨最远,飞越千山万水,直抵北疆流放之地。那县令已被革职查办,原籍百姓自发集资建了一座“寒夜亭”,专为纪念那首四句诗。亭中石碑旁,一名戍边老兵正教孙儿识字,忽见空中一滴墨落于碑面,顺着“官仓米如雪”一句缓缓流淌,竟将整首诗染成深黑色,宛如夜空下的誓言。孩童指着碑问:“爷爷,这字怎么变黑了?”老人沉默良久,道:“因为它终于被看见了。”
就在这一夜,大周境内凡有书斋、学堂、军塾、村塾之处,无论贫富,无论南北,几乎所有人家的油灯都莫名多燃了一炷。更有奇者,许多人家发现自家祖传旧书突然字迹清晰,甚至原本残缺的篇章自动补全。西域商队中的驼夫说,他们在沙漠途中歇脚时,一本破烂账册无风自动,页页翻开,每一页都浮现出不同的批注,笔迹各异,却皆出自《拾字集》中曾被江行舟点评过的作者之手。
而这一切发生之时,拾字庐内,江行舟的气息彻底停止。
江云宁没有哭,只是轻轻合上他的双眼,然后起身,吹灭了桌上那盏陪伴他十载的油灯。
可下一瞬,窗外一道闪电劈下,照亮整间书屋??墙上那支文心笔再度浮起,悬于遗体上方,笔尖垂落一滴浓墨,不落纸,不入砚,而是缓缓滴在江行舟交叠于胸前的双手之间。
墨珠停留片刻,忽然扩散,沿着他掌纹游走,竟勾勒出一幅微缩山河图:江河奔流,城郭林立,书院星布,书声四起。图成之后,墨光一闪,整幅图案沉入他胸口,消失不见。
江云宁怔住,耳边忽闻细微声响??是纸张翻动的声音。
她转头望去,只见地窖入口处,那一捆捆堆积如山的《拾字集》手稿,竟自行松绑,一页页飘起,如蝶舞般盘旋上升。每一页上,无论原先是否有批语,此刻都浮现出新的朱红批注,笔迹正是江行舟生前最后几年所用的瘦劲楷体。
“此论可行,但需更广听证。”
“此人胆识过人,宜荐入监察院试用。”
“诗中有痛,不可轻删,当编入《民间疾苦录》。”
“驳得好!理不在尊卑,而在是非。”
批语纷飞,持续整整一夜。天明时,所有纸张静静落回原处,整齐如初,仿佛从未动过。唯有最上方一张纸上,多了一句从未现世的话:
>“我死后,若有人问我信仰何物,
>请答:我信每一个不肯沉默的灵魂。”
葬礼极简。依江行舟遗嘱,不立碑,不奏乐,不收礼,不发讣告。仅由江云宁扶棺,王陵执绋,张栩捧《拾字集》初稿,三人步行至城外槐林坡??那是他幼年读书之地。坟茔浅埋,覆土后植一株小槐,与拾字庐前那棵遥相呼应。
归途中,王陵低声问:“今后怎么办?没有他,谁来定是非?”
江云宁望着远处炊烟袅袅的村落,淡淡道:“他从不定是非,他只是让是非得以发声。现在,轮到我们了。”
话音未落,忽见一群少年自田埂奔来,手持竹简,满脸激动。为首者高呼:“江先生!我们照您说的办了!昨夜全村集会,把里正贪墨的账目写成了《村讼书》,今天要去县衙递交!”
江云宁点头:“去吧。记得带上副本,留在村中学堂一份,寄往洛阳书院一份。”
少年们齐声应诺,转身疾跑而去。风中传来他们背诵《自由蒙学》的声音,稚嫩却坚定。
自此,拾字庐并未关闭。江云宁仍每日整理门前文章,分类归档,定期送往各地书院、报馆、军塾。她不再代笔批阅,却设下“三问庭”??凡投稿者,须先自问三题:“此言是否出自真心?是否愿负其责?是否经得起万人反驳?”答卷附于文后,方可进入流转。
三年过去,“三问制”遍及全国,成为民间刊文的基本准则。更有好事者统计,十年间大周新增私塾两千七百余所,书坊五百余间,每年刊印书籍逾十万卷,其中八成以上为平民自撰,内容涵盖农事、医方、律例解读、地方志记,乃至女子写的《育儿经》、老兵写的《戍边日记》。
朝廷亦悄然变革。皇帝下令废除“禁语令”残余条款,恢复“谏鼓”制度,并特设“文察司”,专司监督官员压制言论之行为。太子亲自主持编纂《新律疏议》,明确提出:“治国之道,首在通情;通情之要,端在敢言。”
某年秋,江南大涝,灾民流离。一青年书生目睹惨状,愤而写下《哀江南赋》,痛陈官府迟缓、赈粮被扣之事。文章刊发后,地方官欲以“造谣惑众”抓捕,却被当地百姓包围衙门。数百人手持《自由蒙学》,齐声质问:“你们忘了‘不因权贵低头’吗?”
风波惊动中枢,钦差查实后,罢免三名官员。而那书生非但未获罪,反被召入翰林院任修撰,专责舆情收集。临行前,他专程赴拾字庐拜谒江云宁,献上一杯清茶。
“我不求成名,只愿再无人饿死于丰年。”
江云宁接过茶,轻啜一口,笑道:“你知道江先生若在,会说什么吗?”
“请讲。”
“他会说:**你的文章已经替你说了话,不必再求任何人听见。**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