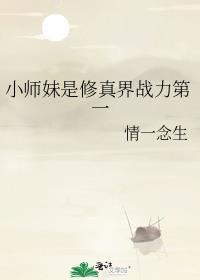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权谋帝王心 > 第70章(第3页)
第70章(第3页)
最后下来的是晟璘,他穿着普通的细棉布袍,虽难掩贵气,却已尽力贴近寻常富家子弟的打扮。
里正早已得了消息,带着几位村老惶恐地迎了上来,便要跪拜。
“老丈不必多礼。”一个清越的声音响起,竟是晟璘抢先一步,虚扶了一下里正的手臂。
他学着楚玉衡平日温和的语气,说道,“我等途经此地,见田亩新垦,生机勃勃,特来看看,叨扰各位了。”
他言语得体,态度谦和,没有丝毫皇室子弟的骄矜,让原本紧张的村民稍稍放松了些。
楚玉衡与萧彻交换了一个眼神,均在彼此眼中看到了赞许。他们没有开口,只是稍稍落后半步,将主导的场合交给了晟璘。
晟璘深吸一口气,压下心中的一丝紧张,开始在里正的引导下,走入村落。
他不再是躲在侍卫身后的惶恐少年,而是主动走向田埂,观看农人耕作,甚至停下脚步,询问今年的秧苗长势,雨水是否充足。
遇到在村口嬉戏的孩童,他会蹲下身,从袖中掏出早已准备好的、用干净桑皮纸包着的几块饴糖,温和地分给他们,并轻声问他们是否识字,可曾想过上学堂。
孩子们起初怯生生,见他笑容真诚,才渐渐围拢过来。
行至一户看起来尤为贫困的人家,见一位老妪正在修补漏雨的茅屋,晟璘驻足,眉头微蹙。
他仔细询问了老妪家中的情况,得知其子参军,家中只剩她与年幼的孙儿,生活艰难。
晟璘沉默片刻,回头看向萧彻,眼中带着询问。
萧彻几不可察地点了点头。
晟璘这才对里正吩咐道:“此类为国出征者家眷,朔州律法应有抚恤与优待,务必落实。此户屋舍,还请里正安排人手协助修缮,所需费用……”他顿了顿,似乎在斟酌,随即坚定道,“从我……份例中支取。”
他没有暴露身份,却以行动诠释了“体恤下情”。
话语虽还带着些许稚嫩,但那份发自内心的怜悯与试图解决问题的担当,却让周围的村民动容。几位村老更是眼眶微湿,连声道:“小公子仁善!谢小公子恩典!”
楚玉衡在一旁静静看着,心中欣慰。他知道,晟璘此举并非完全模仿,而是真正将“民为本”的道理内化于心,开始懂得如何运用自身的权力和资源去践行它。
这便是帝王心术的雏形,非权谋算计,而是仁心与责任的觉醒。
在村中盘桓近一个时辰,收获了大量真诚的感激与拥戴后,三人才辞别村民,信步走向村外一片视野开阔的坡地。
远处是连绵的田畴和辛勤劳作的百姓,近处野花星星点点。
萧彻刻意放缓了脚步,与楚玉衡落在了后面,让晟璘和严锋在前方稍远处走着,给予他们独处的空间。
“如何?”萧彻低声问道,目光落在前方晟璘虽疲惫却挺直的背影上。
“璞玉生辉,已见华彩。”楚玉衡唇角含笑,语气中是毫不掩饰的成就感,“假以时日,必能承载万民之望。”
萧彻侧头看他,阳光下,楚玉衡的侧脸线条柔和,眼眸中映着田野的碧色,因学生的成长而焕发着一种别样的神采。
萧彻心头微动,伸出手,极其自然地替他拂去沾在肩头的一片不知何时落下的细小草屑,指尖状似无意地擦过他的颈侧。
那触碰轻柔却带着电流,楚玉衡身体几不可察地微微一僵,迅速瞥了一眼前方的晟璘和严锋,见他们并未注意,才稍稍放松,耳根却不受控制地漫上薄红,低声嗔怪:“光天化日,萧大将军注意些影响。”
萧彻低笑,收回手,负于身后,指尖仿佛还残留着对方肌肤的温润触感。
他靠近半步,用只有两人能听到的声音说:“影响?我只看到朔州的谋士先生,教导有方,令我……心悦诚服。”
那“心悦诚服”四字,被他念得低沉缱绻,意味深长。
楚玉衡面上更热,瞪了他一眼,却见对方眼中满是戏谑与深情,那点羞恼便化作了无奈的纵容,转头看向远方,只留给萧彻一个泛着红晕的精致耳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