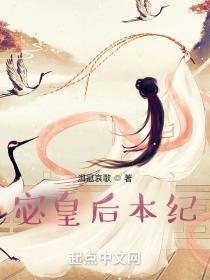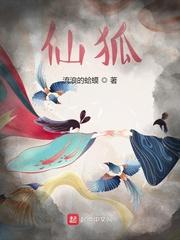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朕真的不务正业 > 第一千零九十一章 嘴上全都是道德文章心里全是生意(第1页)
第一千零九十一章 嘴上全都是道德文章心里全是生意(第1页)
朱翊钧费了天大的劲儿,振武二十三年,新式火铳、火炮、舰炮、野战炮、火药层出不穷的迭代,如此做法,其实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更加方便、快捷、伤亡更小、成本更低的杀人。
当下时代,任何开拓者对低成本、。。。
雨声淅沥,敲在信火书院的青瓦上,如细密鼓点,连绵不绝。林知微坐在堂前,手中捧着那本已翻得边角卷起的《公民问答录》,目光却未落在字句之间。她望着窗外雨幕中隐约可见的铜铃,铃身湿漉漉地泛着幽光,像一只沉默的眼睛,凝视着这片山谷。
小禾蹲在廊下,用炭笔在石板上画着什么。她画的是皇帝赵允熙站在百姓中间,脸上没有龙袍加身的威严,而是一抹疲惫却真诚的笑。她一边画,一边低声念:“他说他不是来救人的,是来听人说话的……可为什么还有人不信呢?”
林知微听见了,却没有接话。她知道,信任从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建立的,它需要时间,需要伤痛后的醒悟,需要一次次被辜负又一次次重建。就像这铜铃,三十年前曾因质疑而响彻山林,也曾因恐惧而沉寂多年。如今它再度轻颤,不是因为所有人都已觉醒,而是因为终于有人敢开口了。
次日清晨,雨势渐歇,晨雾如纱缠绕山腰。书院照常开讲,今日主讲《权力的边界》。学生们围坐一圈,陈启明坐在前排,神情专注。他已不再是当年那个只会愤怒质问的少年,三年来随明理阁奔走四方,亲眼见过改革如何在纸上熠熠生辉,又如何在现实中扭曲变形。他的眼神里多了几分沉重,也多了几分清醒。
“权力的本质,”林知微缓缓道,“不在于它能做什么,而在于它不能做什么。一个国家是否文明,不看它赐予人民多少恩惠,而看它能否容忍人民说‘不’。”
话音刚落,一名学生举手:“老师,可若人人皆说‘不’,岂非天下大乱?”
“正是如此。”林知微点头,“所以我们才需要规则,需要辩论,需要让‘不’的声音经过理性淬炼,而非任其沦为情绪的宣泄。信火所教的,不是反对一切,而是学会为何反对。”
这时,小禾怯生生地举起手:“那……如果连‘反对’本身也被规定该怎么反对,那还算自由吗?”
全场一静。
林知微看着她,忽然笑了:“这是个好问题。甚至比许多大人提的都更接近核心。”
她站起身,走向铜铃,轻轻抚过那道金漆修补的裂痕:“三十年前,我们反抗的是不准提问的朝廷;三十年后,我们警惕的是只准按某种方式提问的社会。前者是压制,后者是规训??而规训往往更难察觉,因为它披着‘进步’的外衣。”
她顿了顿,声音低沉下来:“我怕的不是没人再问,而是所有人都在‘正确地问’,却忘了自己为何而问。”
正说着,远处传来马蹄声。一名信使冒雨疾驰而来,滚鞍下马,递上一封急报。
林知微拆开一看,脸色微变。
西南局势再生波澜。虽有皇帝亲临整顿,贪官伏法、制度重设,但民间积怨未消。近日,一群自称“守屯义士”的退伍屯兵集结于嘉定城外,打出旗号:“还我祖业,废除赎买!”他们焚烧官府文书,扣押督办局差役,声称要恢复旧制,回归军户身份。
更令人震惊的是,这群人中竟有不少曾是信火支持者。他们曾在课堂上高呼“自由”,在辩论中痛斥专制,如今却举起拳头,对抗他们曾拥护的变革。
“他们说,”信使补充道,“信火背叛了最初的理想。你们教我们质疑权力,现在却要用新法律剥夺我们的身份。”
林知微闭目良久,终是长叹一声。
当晚,她召集骨干师生议事。烛火摇曳,映照出每个人脸上的忧虑。
“我们必须回应。”陈启明沉声道,“否则,信火将被视为虚伪之徒,只许自己改革,不容他人反悔。”
“可如何回应?”一名讲师皱眉,“若承认他们的诉求合理,等于否定整个赎买政策;若强硬镇压,又与旧朝廷何异?”
林知微缓缓睁开眼:“答案不在政策本身,而在提问的方式。他们不是反对改革,而是觉得被排除在外。他们问:‘谁决定我们的命运?’这才是真正的叩击。”
她起身,走到地图前,指尖点向嘉定:“明日,我要亲自去那里。”
众人哗然。
“太危险了!”有人惊呼,“那些人已失控,您若落入他们手中……”
“正因危险,我才必须去。”林知微平静道,“当理念遭遇现实的血肉之躯,逃避只会让裂痕更深。我要让他们看见,信火不是高台上的布道者,而是愿意走进泥泞的人。”
三日后,林知微抵达嘉定。
城门外,数百屯兵列队而立,手持农具与旧式刀剑,旗帜猎猎。他们见一辆简朴马车驶来,车上仅有一老妇与一小童,并无护卫。片刻迟疑后,为首者喝问:“可是林先生?”
“是我。”林知微下车,撑伞立于雨中,“我来听你们说话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