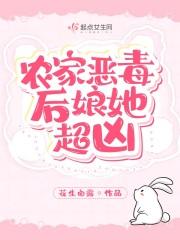书迷阁>毒妃她从地狱来 > 第1183章 白雾可以消失(第2页)
第1183章 白雾可以消失(第2页)
沈砚连夜赶来,带来一张伪造的身份文书和一把短刃。“走吧,”他说,“你还不能死在这里。”
她摇头,将文书推回。“若我走了,谁来告诉人们,真相不该躲藏?”
他盯着她良久,忽然笑了:“你知道吗?十年前我以为你是来复仇的。后来我以为你是来重建秩序的。现在我才明白……你根本不在乎权力,你在乎的是**人心能否记得真实**。”
她轻轻握住他的手:“所以我不能走。哪怕只剩一人听我说话,我也要说下去。”
次日清晨,她独自登上南岭最高的山崖,在巨石上刻下七个大字:“**请记住,你们曾选择遗忘。**”
然后,她点燃了第一把火。
不是焚书,而是烧诏。
火焰腾空而起,映红半片天空。数百名学子闻讯赶来,围聚崖下。她立于火前,声音清越如钟:
“他们怕的不是谎言被揭穿,而是你们开始怀疑。他们怕的不是我讲出真相,而是你们也开始追问。所以今天,我不逃,不藏,不噤声。我要让所有人知道,**记忆不是罪,沉默才是共谋**!”
人群中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有人流泪,有人跪地叩首,更有年轻学子当场撕毁科举准考证,高呼:“宁做真言奴,不做伪史臣!”
三天后,十七个州爆发抗议。农夫放下锄头,匠人停下手艺,书生走出学堂,举着写满往事的竹简、陶片、布条走上街头。他们在城门口堆起“忆山”,焚烧象征遗忘的纸偶,唱起古老的悼亡歌谣。军队奉命镇压,可当士兵听见那些故事??关于饿死的孩子、冤死的忠臣、被活埋的妇孺??许多人放下了刀枪。
甚至有边关将领倒戈,送来敌国密档:原来所谓“百年无敌”的赫赫战功,竟是靠篡改战场记录伪造而成!真正的败仗被说成胜仗,阵亡将士姓名被抹去,只为维持“天朝威仪”。
林小禾收到这些资料时,正在教小女孩们用彩线绣“记忆锦”。她接过密档,翻看片刻,轻声道:“你看,连敌人也知道羞耻了,而我们还在假装胜利。”
沈砚站在门外,听见这话,忍不住笑出声:“你说得对。改变不需要击败镜渊,只需要让更多人不愿再骗自己。”
春天再次降临。
尽管朝廷仍在打压,但忆学堂已在三百余村落扎根。有些地方没有纸笔,村民便用木棍在地上划字;有些地方识字的人少,老人便每天傍晚坐在村口讲故事,孩子们围坐倾听,再转述给下一代。一种新的传统正在形成??不是由权力书写,而是由普通人守护。
林小禾开始撰写《民忆通鉴》,收录来自全国各地的记忆碎片。其中有悲,有怒,也有温情:一位母亲记下儿子参军前夜偷偷塞给她的一块糖;一位老兵回忆战友临终前托付的家书从未送达;甚至还有一位宦官忏悔自己曾亲手销毁三十八位宫女的遗言……
这本书没有序言,只有扉页上一行小字:“献给所有未被听见的声音。”
某夜,她伏案疾书,忽觉袖中骰子微热。取出一看,六面缓缓旋转,最终停在“醒”字上。与此同时,窗外电光一闪,暴雨倾盆而下。
她起身推开窗,风雨扑面而来。远处海面上,一艘忆舟正破浪前行,桅杆顶端挂着一盏永不熄灭的真忆灯。
她忽然想起梦境。
梦中,她走进一片无边的迷雾森林,脚下踩着累累白骨。忽然有人从雾中走出??竟是年轻的沈砚,手里拿着那片烧焦的纸。他说:“你迟到了一百年。”她问:“谁等我?”他答:“所有人。”
醒来后,她便决定写下这本书。
此刻,雷声滚滚,仿佛天地共鸣。她提笔在《民忆通鉴》最后一章写下:
>“历史从来不是过去的事,而是我们如何对待过去的方式。
>若人人皆可言说,则无人能独裁记忆。
>若代代相传,则黑暗永不得重生。
>我不信救世主,只信每一个敢于记住的人。
>此书不成经典,亦不求流传千古。
>唯愿百年之后,仍有孩童捧卷而问:
>‘从前真的有人不敢说话吗?’
>而他们的父母,能坦然回答:
>‘是的,但他们最终学会了开口。’”
笔落,雨止。
晨曦初露,照在桌角那枚水晶骰子上,“醒”字熠熠生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