书迷阁>1987我的年代 > 第696章认命求月票(第2页)
第696章认命求月票(第2页)
她忽然注意到尸骨手指微微弯曲,似乎临终前紧紧攥着什么。小心翼翼掰开指骨,一枚锈迹斑斑的铜铃落入掌心。
“叮……”一声轻响,在寂静山谷中格外清晰。
那一刻,仿佛有风吹过千年时光。
“走吧。”她收起铜铃,声音沙哑,“别让他们白白死了。我们要活着走出去,带着他们的路。”
再往前,地势愈发险恶。一处陡坡几乎垂直,他们只能用绳索固定身体,逐个攀爬。途中,小周一脚踏空,幸亏老陈反应快,一把拽住背包带,才没摔下深渊。他的脸惨白如纸,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。
“怕就喊出来。”老陈拍拍他肩,“哭也行。在这儿没人笑话你。”
小周终于哽咽:“我不想死……我还想回家看我妈……”
“不会死的。”林小满递给他一瓶水,“听着,你现在每走一步,都是在为别人开路。那些母亲、那些孩子,她们需要你手上这台机器。你不是为自己走,你是替她们走。”
他抹了把泪,点头,继续前行。
正午时分,他们终于翻越主山脊,眼前景象骤变:云海翻腾之下,一条深邃峡谷横亘东西,怒江如银蛇蜿蜒其间。对岸半山腰,几十户木屋依崖而建,屋顶飘着袅袅炊烟。一群妇女正列队上山,每人背上都压着高高的柴捆,身形佝偻,步履蹒跚。
“到了。”林小满眼眶发热。
他们原地休整两小时,用卫星电话联系后方车队更改路线。傍晚前,全员抵达临时落脚点??乡政府设在山脚的护林站。站长是个五十多岁的退伍兵,姓张,见到林小满一行人竟真从“鬼见愁”走出来,震惊得说不出话。
“你们……是铁打的?”他喃喃道。
“不是。”林小满笑,“是心里装着比命更重要的东西。”
当晚,她顾不上疲惫,立即召集村民代表开会。来的大多是妇女,脸上刻着风霜,双手粗糙皲裂。一位名叫娜香的母亲抱着六个月大的婴儿参会,背上还残留着长期负重留下的紫红色勒痕。
“我们试过各种办法。”她说,“用布带绑孩子,一手拎柴一手扶腰。可年纪越大,越走不动。我婆婆五十岁就瘫了,医生说脊椎压坏了。”
林小满让阿杰拿出电动助力背架原型机,现场演示使用方法。这是一种轻量化外骨骼装置,通过电机辅助减轻背部压力,特别适合山区负重行走。当娜香第一次将柴捆放在架子上,感受到力量被分担的瞬间,她愣住了,继而泪水夺眶而出。
“这……这能让我不再瘸吗?”
“不仅能。”林小满握住她的手,“还能让你挺直腰,牵着孩子上学。”
会议决定,首批十台样机留在寨中试用,由林小满团队培训本地妇女操作与基础维修。同时建立“背架互助组”,谁家用完就传给下一家,形成共享机制。
第二天清晨,第一堂技术课在晒谷场举行。二十多名妇女围坐一圈,认真记笔记。有个叫阿依的女孩才十六岁,眼神明亮:“老师,学会这个,我能去外面工作吗?”
“当然。”林小满点头,“你还可以教更多人。将来,这里会有属于你们的‘萤火工坊’,生产自己的背架,卖给别的山寨。”
女孩笑了,露出一口整齐白牙。阳光洒在她年轻的脸上,像一朵初绽的山茶花。
午后,林小满独自走访了几户人家。在一栋摇摇欲坠的木屋里,她见到了一位卧床三年的老妇人。她是村里的接生婆,一生接引三百多个新生命,如今却因风湿瘫痪,日夜忍受疼痛。
“我没用啦。”老人叹息,“连尿桶都端不动。”
林小满打开“萤火盒子”,连线成都康复科专家。高清影像传输成功,医生根据症状开具理疗方案,并指导家属如何用简易器械进行关节活动训练。
“奶奶,您还会站起来的。”她轻声说。
老人浑浊的眼中闪过一丝光亮:“你说真的?”
“我说真的。”她握住那只枯瘦的手,“而且,我要请您当‘萤火学堂’的第一位荣誉教师,教孩子们认草药、讲山里的故事。”
老人怔住,许久,嘴角缓缓扬起。
第三日,暴雨如期而至。山洪暴发,通往外界的唯一土路彻底中断。但他们早已预料,提前储备了七天物资。更令人振奋的是,经过调试,太阳能基站终于稳定联网,“云端课堂”首次接入寨中小学。
教室里,六个年级共三十一名学生挤在一起。投影仪亮起那一刻,所有眼睛都睁大了。屏幕上,上海某小学音乐老师弹着钢琴,教唱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
孩子们怯生生地跟着哼唱,跑调却真诚。阿依站在最前排,声音最大。林小满站在窗外,听着这稚嫩歌声穿透雨幕,忽然觉得,这比任何交响乐都动人。
课后,她召集全体队员召开紧急会议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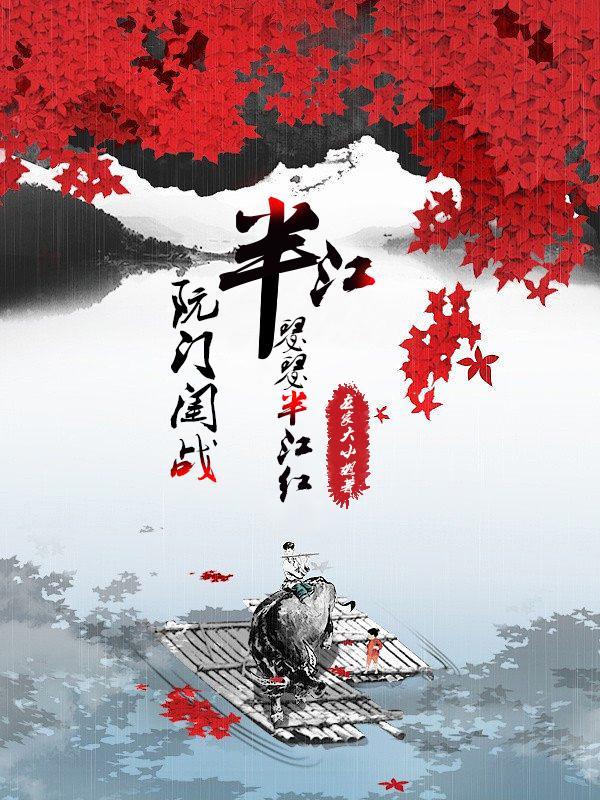
![把惊悚游戏玩成修罗场[无限]](/img/62986.jpg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