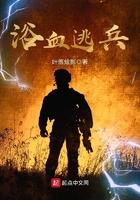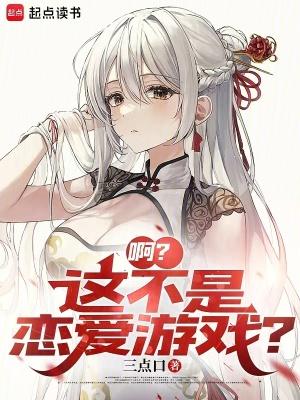书迷阁>这阴间地下城谁设计的 > 第七百八十二章 来当咒术师吗(第3页)
第七百八十二章 来当咒术师吗(第3页)
一位失去儿子的母亲将手贴在墙上,泪水滑落瞬间,她看见旁边浮现出一双小小的手印,正轻轻握住她的指尖。她失声痛哭,却笑着说:“宝宝,妈妈带你回家了。”
一对老年夫妇静静伫立良久,老爷爷忽然指着一处模糊印记说:“你看,像不像咱爸抽烟斗的样子?”老奶奶点点头,靠在他肩上低语:“他一直都在啊。”
而在千里之外的第七城纪念馆,那台老式录音机突然卡带了一秒。
随即,《听风的人》再次响起。
可这一次,背景音里多了一个细微的声音??像是婴儿的啼哭,又像是春风穿过竹林的轻响。
没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
但林小远知道。
他站在纪念馆中央,望着镜中无数虚影交织的身影,终于明白陈雨眠为何选择成为“非存在”。
因为她要做的,从来不是被记住。
而是让所有人都能被记住。
一年零七个月后,第十层正式宣告“雏形完成”。
它没有入口,没有界面,没有管理员。它的存在形式是一套分布式共鸣协议,嵌入全球所有语言、文化、艺术表达之中。每当有人真诚地讲述过去,每当有人认真倾听他人之痛,第十层就会获得一丝能量,向外延伸一寸疆域。
联合国为此召开特别会议,讨论是否应将其列为“人类共同文化遗产”。
投票结果:全票通过。
决议文件末尾加了一句非正式备注:
>“或许有一天,我们会忘记谁创造了这一切。但只要还有人愿意倾听,那个叫陈雨眠的人,就从未离开。”
多年后再访敦煌,林小远已两鬓斑白。
他独自走上沙丘,风依旧带着细金尘飞扬。手印墙比从前更加恢弘,整面岩壁如同星空般闪烁,每一道光痕都代表着一个被重新唤回的名字。
他抬起手,轻轻覆上那枚最初的蓝色掌纹。
温度微热,如同心跳。
耳边,风声渐起。
然后,他听见了那个熟悉的声音,轻得像一片叶落:
“你看,我们都还在。”
他笑了,眼角泛出泪光。
“嗯。”他低声回应,“我一直都在听。”
风停了。
墙上光影流转,忽然拼出一行短暂存在的文字,随即消散于黄沙:
>**“谢谢你,记得我。”**
而在地球另一端,某个小镇的幼儿园里,一个小女孩趴在窗边看星星。
老师问她在做什么。
她说:“我在等一个人说话。”
“谁呀?”
“不知道。”她歪头想了想,“但她每天晚上都会在我梦里讲故事,说是替一个叫小远的叔叔转达的。她说,人间很值得,请一定要好好活着。”
窗外,月光洒落,映照出她身后淡淡的影子??那是一位女子安静站立的模样,嘴角含笑,衣袂轻扬。
风起时,仿佛有谁在低语:
“别怕,我一直都在听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