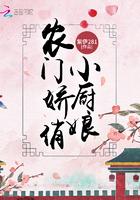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众仙俯首 > 第457章 果然东西还是要抢着才好吃(第1页)
第457章 果然东西还是要抢着才好吃(第1页)
夜幕初垂,华灯点亮了青木城的街巷。
房间里,孤男寡女,气氛愈发暧昧起来。
苏羽瑶想起这些天与林落尘的亲密接触,浑身不自在,连忙站起身。
“时间还早,我们出去走走吧?”
林落尘自然无所谓,他也正想探查一下城中的情况,省得遇到魔族逃都不知道怎么逃。
片刻后,两人并肩走在熙攘的街道上,两旁店铺灯火通明,人声鼎沸。
这座青木城规模不算大,但因着云舟渡口的存在,倒也商贾云集,颇为繁华。
虽城外闹鬼的传闻弄得人心惶。。。。。。
海风又起时,沈知意正坐在九渊谷外的山脊上。她已走出七日,脚步却未停歇。身后那座万言钟沉入云雾,仿佛被天地收回了呼吸,只留下一道淡淡的光痕,在晨曦中如丝线般飘散。她的玉佩贴在心口,温润依旧,可其中流转的光却比往日黯淡了几分??像是耗尽了某种积蓄百年的力量。
她不回头,也不愿回头。
阿砚走了,不是消散,而是归去。他的残魂随最后一缕琴音融入地脉,化作镇守第九层封印的永恒回响。他不再需要肉身,也不再需要言语,因为他已成了“听见”本身。而她,终于不再是那个只能承接沉默的容器。
但她知道,这并非终结。
山下村落炊烟袅袅,几缕黑烟夹杂其间,似有火光闪烁。沈知意起身下山,脚步渐急。走近才知,是村中一座祠堂被人纵火烧毁。族老跪在废墟前痛哭:“祖宗牌位全没了!谁来替他们说话啊!”
旁边妇人抱着孩子低声啜泣:“我男人昨夜登了启心台,说了句‘税太重,活不下去’,今早就被抓走了……他们说这是煽动民变。”
孩童不懂事,在灰烬里翻找半焦的木片,忽然举起一块刻着名字的残牌:“娘,这是爷爷吗?”
妇人接过一看,猛地抱住孩子嚎啕大哭。
沈知意站在人群之外,静静看着这一切。她从袖中取出那本无形之册,轻轻翻开一页。上面浮现一行字:
>“我不是想造反,我只是想让孩子吃饱饭。”
那是昨夜某个农夫临被捕前所思,尚未出口,已被她拾取。
她合上册子,走向祠堂残垣。众人见她到来,纷纷让开一条路。有人认出她是曾在南方教书的哑女先生,便低声道:“听说她能让死人的话活过来……”
沈知意蹲下身,指尖轻抚焦土,闭目凝神。片刻后,她缓缓写下几个字于掌心,然后摊开手,迎风一扬。
刹那间,灰烬腾空而起,如蝶舞旋。每一片都映出一张面孔??老者、少年、妇人、婴儿,皆是此村百年来逝去之人。他们的嘴唇无声开合,却有一道道微弱的声音自空中响起:
“我种了一辈子田,没偷过一粒米。”
“我死前还在织布,为的是儿子娶妻。”
“我没读过书,但我信公道。”
“你们活着,别替我们沉默。”
声音虽细,却穿透人心。村民一个个跪倒在地,泪流满面。连那抓走丈夫的差役也呆立原地,手中铁链哐当落地。
沈知意转身离去,身后传来一声嘶喊:“先生!您到底是谁?!”
她没有回答,只是将一枚贝壳放在祠堂门槛上??那是她从海边带来的信物,孩子们曾用它串成风铃。贝壳微微发光,随即碎裂,化作一道银线,渗入大地。
三日后,这座村庄的名字出现在帝都《启心录》榜首。朝廷派使臣前来查访,不仅释放被捕农夫,还减免三年赋税。更奇的是,每当夜深人静,村中井水泛起涟漪,水面竟浮现出历代祖先的影像,低声叮嘱子孙:
“要说真话。”
“莫怕。”
“我在听。”
消息传开,九州各地掀起一股“拾言潮”。百姓自发搜集遗落的话语??坟前未烧尽的祭文、墙角褪色的控诉帖、牢狱中指甲刻下的血书……尽数送往各地新建的“言冢”。这些话语被供奉于地下水晶室中,由专人抄录、诵读、传承。有人质疑此举是否过于狂热,一位老儒却叹道:“百代禁声,一朝迸发,何足怪哉?若连痛都忘了喊,人与石像何异?”
沈知意一路北行,穿行于这样的城镇之间。她不再停留太久,唯恐自己成为新的图腾。她不愿被人膜拜,只想让那些话自己站出来,像野草破土,像春雷惊蛰。
然而,越是靠近北方边陲,空气中的话语就越沉重。
某夜宿于荒庙,她梦见自己站在无尽深渊之上,脚下是层层叠叠的嘴,张着,喊着,却发不出声。忽然,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:“你救得了他们吗?”
她回头,看见阿砚坐在断碑上,神情罕见地冷峻。
“我能听见。”她默然回应。
“听见不等于拯救。”他说,“有些人,宁愿永远不说,因为怕说出来之后,世界仍不在乎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