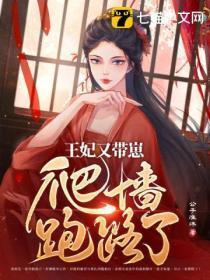书迷阁>为变法,我视死如归 > 第262章 朝堂之变(第1页)
第262章 朝堂之变(第1页)
王小仙赶到宫门的时候恰好看到王安石从宫里出来,没有骑马,而是略微有些佝偻,脸色上有着很明显的疲惫,与平时一定要骑着高头大马出入宫禁的风光模样简直是判若两人。
王安石见了王小仙也不意外,只是笑着跟。。。
风雪再度掠过嘉峪关的城堞,却已不再如往日那般凛冽刺骨。城楼之上,一面崭新的旗帜在晨光中缓缓升起??红底金穗,中央是一轮初升的太阳,下方刻着“共和”二字。这是第一面正式悬挂于边关要塞的共和国旗,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与另一个时代的开启。
赵昭站在旗杆下,身披一件素色长袍,再无龙纹加身。他仰头望着那面迎风招展的旗帜,眼神平静如水。柳素娥立于其侧,轻声道:“您真的决定了?三年后,彻底离开权力?”
“不是离开,是归还。”他微微一笑,“这江山不属于某一个人,它属于每一个修渠引水、背书上学、在灯下写信给远方孩子的普通人。”
话音未落,远处传来马蹄声急。一名青年军官翻身下马,军装笔挺,肩章上绣着“国民警备队?西部支队”。他敬礼道:“主席阁下,敦煌民生渠今日全线通水,百姓自发集会庆祝。林婉清院长来电,说田小禾带领女子工程队完成了最后三公里混凝土浇筑,渠水已流入干涸百年的绿洲。”
赵昭闭目片刻,仿佛听见了水流奔涌之声。那不是普通的水声,而是大地苏醒的脉搏,是无数母亲不必再为孩子煮树皮汤的希望之音。他睁开眼,点头道:“告诉她们,我听到了。”
回京途中,沿途村庄张灯结彩,不为帝王寿辰,而为“共和节”的设立。街头巷尾张贴着新颁布的《公民权利法案》摘要:人人平等,信仰自由,言论有护,劳动受偿。孩子们在学堂里朗诵:“我们不做奴才,我们要做主人。”女童入学率首次超过男童,因偏远地区专设“流动女师班”,由退役女警护送教师进山授课。
抵达京城时,已是深夜。紫宸殿早已更名为“中央议事厅”,门前石狮被移走,换成了两尊手捧书卷与铁锤的青铜雕像,题曰:“知识与劳动,共铸国魂。”
赵昭并未直接入内,而是绕道去了城南贫民区。这里曾是乞丐与流民聚居之所,如今已被改造成“新民社区”。整齐的排屋依街而建,每户配有独立厨房与卫生设施,屋顶架设太阳能热水器。社区中心设有公共食堂、阅览室与医疗站,夜间仍有老人围坐读报,学生伏案自习。
他在一户人家门口停下。门牌写着“崔承志寓”。推门而入,屋内陈设简朴却整洁,墙上挂着一幅手绘地图??标注了全国历年冤案发生地。崔承志正伏案疾书,鬓角已染霜白,听见脚步声抬头,见是赵昭,起身欲拜,却被一把扶住。
“不必行礼了。”赵昭拉过椅子坐下,“现在你是史官,我是待卸任的旧君。”
崔承志苦笑:“若非亲眼所见,我永不会信,变法竟能如此深入骨髓。”
“你写的《近代冤案录》初稿我看过了。”赵昭从怀中取出一册批注本,“你在‘戊戌清算案’中提到,当年七十二名新政官员被斩首示众,家属流放极北苦寒之地,其中一人之女,被迫为婢,十七岁自尽于井中……”
崔承志声音微颤:“那是家母。”
赵昭猛然怔住,良久无言。烛火映照着他脸上的沟壑,像是岁月刻下的碑文。
“我不知道……”他终于开口,嗓音沙哑,“若早知她是你的亲人,我是否还能写下那道处决令。可那时,旧党反扑太烈,我不杀他们,他们便要毁掉一切改革成果。”
崔承志摇头:“不必道歉。我不是来讨债的。我只是想让后人知道,每一次变革背后,都有血泪。哪怕初衷为民,手段亦可能伤及无辜。所以,我们必须记住,而不是遗忘。”
赵昭凝视着他,忽然笑了:“你比我更适合写这段历史。”
当夜,二人促膝长谈至天明。崔承志讲述了自己十年逃亡生涯:如何靠抄写佛经维生,如何目睹妹妹被人贩子拐卖后跳崖明志,如何在海外接触启蒙思想,最终明白复仇无法复活母亲,唯有制度才能阻止悲剧重演。
“所以我愿意放下刀剑,拿起笔。”他说,“用真相代替仇恨,用记录代替报复。”
赵昭默默记下每一句话,临别时只留下一句:“明年春,我将亲自赴甘肃,为所有在改革中蒙冤者举行公祭。他们的名字,要刻进国家纪念碑。”
翌日清晨,中央议事厅召开特别会议。议题只有一个:《共和宪法草案》审议。
大厅内座无虚席。三百名代表来自各省,有工人、农民、教师、医生、女工代表、少数民族长老、归国华侨。他们穿着各异,却都佩戴统一徽章??圆形铜牌,正面刻“民权”,背面印“责任”。
赵昭作为临时主席发表开场演说:
“十年前,我说要变法。有人骂我篡位,有人称我疯魔,有人断言中国不堪改革。今天我们坐在这里,不是因为胜利,而是因为坚持。因为我们相信,人民可以治理自己的国家,不需要皇帝代言。”
台下掌声如雷。
草案逐条表决。最关键的第五条:“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,通过普选产生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机构。”以298票赞成、2票反对、5票弃权通过。反对者是一名前清遗老和一名保守派学者,理由仍是“民智未开,恐生乱局”。
赵昭并未驳斥,只是请他们观看一段影像??由新闻纪录社拍摄的武汉平民大学课堂实况。镜头中,一群衣衫朴素的学生正在辩论“联邦制与单一制利弊”,一名盲人女生手持盲文打字机发言:“我认为分权不等于分裂,就像眼睛看不见,心仍能感知光明。”
放映结束,全场肃然。那位遗老低下了头。
散会后,柳素娥递来一份密报:朱鸿儒在狱中绝食抗议,声称“宁死不受叛国审判”。
赵昭沉吟片刻,提笔批复:“准其绝食,但每日记录身体状况,公开发布。让他选择死亡的方式,也让我们看清极端主义的本质??它连生命本身都不尊重。”
三天后,消息传出:朱鸿儒停止绝食,要求阅读《公民权利法案》。又三日,他写下万言悔过书,承认自己被仇恨蒙蔽,误将倒退当作忠诚。
赵昭批示:“允许他在监狱图书馆任教,讲授历史与政治哲学。让后来者看到,觉醒永远不晚。”
冬去春来,全国首次县级普选启动。投票站设在学校、祠堂、集市甚至船上。选民手持身份证与选民证,在监票员见证下投入密封票箱。农村地区采用“红布遮眼、黄豆计票”传统方式,确保文盲也能行使权利。
结果揭晓当晚,央视直播开票过程。最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在贵州深山:一位百岁苗族老妇,在孙女搀扶下步行十里山路来到投票点。她不会写字,却坚定地在候选人照片下按下红色指印。记者问她为何坚持,她用方言说:“我活了这么久,第一次觉得自己算个人。”